《方形》剧情介绍
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 Claes Bang 饰)和妻子离婚后,带着小女儿(Lilianne Mardon 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克里斯蒂安在一间艺术馆里担任策展人的职位,最近,他正在筹划一项名为“方形”的装置展览,希望宣扬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积极向上的理念。 一场意外中,克里斯蒂安的手机被偷了,通过GPS定位,克里斯蒂安找到了偷手机的小偷所居住的公寓,深夜里,克里斯蒂安向该大楼的每一户居民家的门缝里塞进了一张指控书,哪知道这不经思考的举动,为他惹出了大麻烦。为了宣传展览,克里斯蒂安找来了传媒公关公司的代理人,哪知道这两个不靠谱的男人,很快就将这个展览搅成了一锅粥。祸不单行,克里斯蒂安和女记者安妮(伊丽莎白·莫斯 Elisabeth Moss 饰)之间的一段露水情缘让安妮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末世西游之二郎神传奇箱男奢华美杜莎与你的暖暖时光新米炼金术师的店铺经营蜀山战纪之剑侠传奇金蚕丝雨龙门镇客栈向阳而生智深传2光新婚公寓最好的岁月视界不方便的记忆我家大师兄有点靠谱料理仙姬狙击者2飘落的羽毛超能力大战印度超人3鲜浪潮.语2021大侦探波洛第十季仙班校园2怀疑苏梅之歌JOJO的奇妙冒险石之海Part.2夜魔附身钢铁苍穹2:即临种族芭比之美人鱼历险记2
《方形》长篇影评
1 ) 一场演绎艺术概念的行为主义表演
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作为70后中生代中流砥柱,自跻身戛纳、柏林金熊、东京电影节,近年来可谓顺风顺水。
2014年的《游客》更是大放光彩,至本片《方形》达到导演职业生涯巅峰——在艺术电影的圣坛第70届戛纳电影节摘得金棕榈。
奥斯特伦德以其极为鲜明的创作风格辨识度,在当今艺术电影的范畴中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片名《方形》取自于皇家博物馆的一个艺术装置,在博物馆门前用灯管围城一个正方形,寓意是信任与关爱的圣所,其原则是“在它之内我们共享权利、同担义务。
”围绕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浓缩哲理意味的高概念,以博物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为中心,辐射出(方形)圈里圈外的众生相,把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升华成一场集体演绎艺术概念的行为主义表演。
生活优渥的克里斯蒂安是精英阶层的典范,因手机被偷卷入一系列看似荒诞离奇的事件之中——放下身段去塞恐吓信,失而复得之后又被底层男孩斥责纠缠,继而遭到一夜情对象的质疑,“大猩猩”在酒会上表演引发混乱,运作的“方形”项目因营销不当而被围攻最终辞职。
影片文本内容极为丰富,指涉对象多元,以知识分子独有的气韵戏谑名流生活,营造高级的尴尬美学,讽刺力量十足,冷幽默处处让人如坐针毡。
中产阶级的尴尬假面本片很容易联想到布努埃尔的传世名作《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以荒唐的喜剧手法剥离中产阶级衣冠楚楚的假面,讽谑轻灵、古灵精怪的配乐如灿烂咏叹调,在批判意味之外悄然涌现喜剧因子。
片中的中产阶级无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尊重」姿态对待社会意义层面的“弱势群体”——底层劳动者、移民群体、残障人士、有色人种……彬彬有礼的节制与容忍裹着厚重的钟形罩,礼仪必须放置在设置好的安全距离之内,粗鲁和猥琐须隔绝在面具之外,每个人都须得确保自己的合理、干净、文明。
大家在广场上行色匆匆,即便听到求救,明哲保身才是第一要义。
而克里斯蒂安的仗义显然并非出于真正的同情,而是彰显个人文明标识的时机,当然他很快就迎来好心不得好报的尴尬境地。
更尴尬的是,当他以“落魄英雄”的身份向行人借手机时,得到的是毫不犹豫的拒绝。
此刻的克里斯蒂安心中必定后悔方才的热情,亦正是钟形罩存在的必要性。
短短一场戏接连两个反转,戏剧张力在开场不久就得到释放。
151分钟内,克里斯蒂安遭遇或参与的无数尴尬与剧情走向贴合,不仅逐渐丰满个人形象,也折射中产阶级的处事哲学。
从与下属意气风发共谋恐吓信,到互相推诿不肯亲身执行,凸显人际关系的脆弱疏离。
与女记者一夜情的反应,显示出他的自命清高——即使有过亲密关系之后,依然保持个体的“独立”,作为极隐私存在的精液怎能轻易交出?
在克里斯蒂安看来,如若给出无异于卸甲交心,绝非遵循游戏规则的上流精英所为。
艺术家采访座谈上的秽语连篇,虽让在座的西装革履们难以忍受,但为了以示自己的宽容尊重,大家须充耳不闻——毕竟人家是罹患秽语症的“弱势群体”。
这与克里斯蒂安为流浪者买汉堡反遭奚落一样,往日的惯性歧视在矫枉过正的大环境里,反向扭转成另一种歧视——“弱势群体”反而站在道德制高点,平权意识已经饱和到逆向流转。
基于此,“方形”项目的营销团队,采用典型的瑞典主流社会形象来制造话题噱头,他们并无勇气以有色人种或其他种族作为视频主角。
假面的真正脱落是酒会上“大猩猩”对精英们的挑战,游戏规则是:“设想身处丛林与野兽相遇,须保持屏气凝神才能逃过一劫,静待他人成为野兽的盘中餐。
”规则本身就具有阶级固化的性质。
很快,人们从游戏的欣喜中抽身,逐渐演变成讪笑、厌恶、惧怕,甚而逃离现场,文明和礼节在兽性面前节节败退,装作尊重的假面纷纷崩溃,直至表演“大猩猩”的表演者失控,触及高贵人们的底线,才群起攻之。
艺术作品的失语境地当广场前的骑士青铜像轰然倒塌,代之以灯管的简单装置,印证着集结思想智慧与手工创作之美的古典作品在展览场域里的退场。
艺术不再追求具有高品格的轮廓外象,不再承载具有思辨意义的功能属性,当代艺术转向对日常事物的开发,让日常物品焕发艺术的光彩和意义,让艺术品占据大众视野,而不再是特权阶级的特供品——这与上文所述的尊重姿态吻合。
但所谓的“放低姿态”,仅仅是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
开幕酒会上,克里斯蒂安关于艺术的演讲显然和自助餐的美味难以匹敌,华服端庄,道貌岸然,然而一听到厨师宣布开餐,先前端着的姿态纷纷抛却,艺术毕竟难以果腹。
开场时女记者采访克里斯蒂安问到“在博物馆展示一件物品时,它是否就自动成为了艺术品?
”这个问题触及到当代艺术展览最尴尬的本质,在现实中经常听闻无心之误的摆设竟引发观赏热潮。
克里斯蒂安也用到此招“把您的包摆在这里”,相当巧妙地规避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如何判断一件物品是否是艺术品,还是日常用品?
所谓“艺术价值”究竟是事物本身拥有的属性,还是人为赋予的价值?
其间的差异是否为大众所察觉,还是特定范畴内的权威制定标准?
这个似乎无解的问题,在清洁工不小心损坏另一个装置《You have nothing》时得到迅疾的解决——按照片摆好就行!
经工作人员重新摆放的作品,即使原样复刻,也已与原作者的创作发生位移,还能称之为“艺术品”吗?
以克里斯蒂安的眼光来看并无差异,毕竟“最先锋的艺术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毕竟“艺术”是可以购买的;而在大众的眼里,因为看不出样貌的差别,也永不可能有窥出差异的机会。
于是,艺术作品的定义面临着失语的境地。
而艺术品一旦成为策展的商品,被摆上货架待资方估价,它必须再次转换身份,扁平为新媒体时代被广泛迅速传播的信息。
从此,艺术不再拥有瑰丽的光环,也不再具备温凉可感的情感质地,只是信息海洋里的沧海一粟,是吸睛的工具,还可能是投注廉价同情的符码。
方形符号的解锁方式“方形”(square)不仅是艺术装置作品,也是测试人性的试验剂,更是全片的题眼。
博物馆地处square(广场),涉及双关的指涉,在显性视觉特征和隐性指代内容之间建构起关联。
「方形」的意图是建立一个虚拟的精神契约:圈内者须互相信任,彼此平等。
反讽的是,影片中信任几乎完全缺席,平等也只剩虚假的外衣。
方形的概念贯穿始终,除了实体意义的灯管方块,有三处楼梯的特写亦呈「方形」。
克里斯蒂安走入居民楼时的漩涡楼梯俯视,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出方形;与男孩争执后失手误推,忐忑瞠视的楼梯空镜;以及结尾和两个女儿去道歉,一起走上楼梯的旋转方形。
三个放大的「方形」是剧情出现转折之处,在节奏的切分上具有明显的间隔作用。
克里斯蒂安在以为手机事件解决后,又接到便利店电话,声称另有包裹给他,此时他处于一个「方形」取景框里,意味着他将再次被困囿。
女儿参加跳舞队,也在一个「方形」之内,教练说:“要把心思放在团队。
”可以说是「方形」概念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女孩们被圈在「方形」里,从此成为一个共享体,成为其中一员,才能被认可,才算是融入这个群体。
于是,「方形」围城的城里城外,都成为这场行为主义的群演。
载于《看电影 2018·2》
2 ) 电影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展览
这部讽刺展览艺术的电影本身也可以视为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展览,频出的事件基本都被处理成了一种现象式的隐喻,有鲜明的符号性和指向义,现象之间的逻辑也是弱相关的,并不构成特别连贯的叙事,而对一个隐约的共同主题有所呼应。
导演已经将尴尬美学操作得十分娴熟,成为他惯用的一种腔调,让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心态满拧的普通人突然间被卷入公共秩序,利用时间差制造了自顾不暇的窘迫,并无差别讽刺所有人。
讽刺集火于社会关系中的“道德成见”,以“square”代表的方形和广场为喻体,途径广场的策展人在蓄意谋划的一出闹剧中被偷了钱财物品后,选择进入方形的旋转楼梯挨家挨户塞匿名威胁信要求归还,表达他作为半个公众人物的、欲说还休的进犯,是在已经崩塌的信任机制的废墟上跳舞,必然会失败。
有很多现象成对出现,家里的宠物猩猩优雅地涂口红、看画册,初显“人性”,宴席上受邀表演模仿猩猩的人类艺术家全情投入,“兽性”爆发;广场上人们对乞丐视而不见,反之乞丐对递来的食物理所当然;室内的人们对怀中婴儿聒噪的哭叫充耳不闻,网络上的人们对以孩子为卖点的艺术展宣传片揭竿而起;媒体对哗众取宠的艺术营销大加批判,转头又为打响名声的艺术展做起广告。
也有个别现象被编织进图景里,与女记者一夜情后甩不掉的猜忌,艺术访谈上观众止不住的“秽语症”,被不懂艺术的清洁工破坏了一角的沙砾展品等等,构成了对不规则的私有制意识、被破坏的公共规范的零星透视。
策展人以守序、善良为动机,却落得迟到一步、处处错位的境地,他策划的以人人互助为题旨的艺术展览,更是成为一处被各色扑朔迷离的现代现象架空的空间。
但能被解读,仅仅意味着电影提供了可供解读的意图,并不代表它很好地完成了这一意图。
导演的讽刺并不雄辩,而是语境涣散的、隔靴搔痒的讽刺,和《悲情三角》观感相似,依旧显得小家子气。
电影热衷于堆砌现象,叙事却很失焦,像是乍看文笔精致、细看缝合感很重的美文,局部大于整体,荒诞性并未从根源立住。
电影常常深陷于刻画一种奇观中,忘记适时收手,像是观众已经停住了笑,剩下导演又径自笑了很久,很大一部分尴尬感由此得来。
总的来看,电影的讽刺显然带有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气质,十足的优越感令自我解嘲有了自我陶醉的意味,以至于电影看上去更像一种圈内人的、沙龙式的娱乐。
3 ) 那麼方形之外呢?
主策展人結束講話,廚師長剛走上階梯開始介紹當日菜單,台下的知識分子和中產精英們便紛紛離席,於是他忍無可忍,大吼一聲。
(現實中的精英名流即使不耐煩,也會維繫姿態老老實實舉著酒杯站著聽完吧。
)開頭女記者丟出的一長串連主角都聽不懂的「當代藝術用語」,文人雅士義正言辭談論著社會責任與平等關懷,走出美術館卻與伸手求援的募款志工擦肩而過,即使這些荒誕、偽善與冷漠真實存在著,觀看過程中這些令人捧腹的諷刺細想起就變得極為刻意。
到再後來清潔工居然意外清掃走了藝術品,影片提出疑問「擺放進美術館的東西就成為了藝術品嗎?
」不談ready-made,幾年前也有過參觀者把自己的眼鏡放在展覽角落聲稱那是藝術品的事件,我逛美術館的時候也有過錯把館內設施當做展覽的一部分甚至煞有介事地給它拍照的經歷。
「藝術是否可以被定義?
」或者再進一步的「何為藝術」這類問題雖老生常談,卻始終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
昨天在《Art in Context: Rethinking the New World》里的一章中讀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最初建立時的故事,館里放滿了為了「提升」工人階級品味的石膏複製品,可博物館卻不在週日開放,而週日則是紐約市工人階級人群唯一的休息日。
一方面,複製品是否能真正替代原作起到「教育」作用還無法定論。
另一方面,這樣的「教育」不僅因沒有實際為人考慮而顯得偽善,而「教育」本身也好像只是上層階級自以為是對「野蠻人」的開化行為。
之後「野人」真的出現在社會名流的宴席上,作為觀者的我無法確認這到底是表演設計還是現場失控,文明又懂得欣賞藝術的高知人群不知所措卻故作鎮定的模樣也顯得好笑又可悲。
有人會從「野人」行為激起「文明人」的混亂與獸性的角度來解讀這一幕,我卻在想,為什麼他們花了那麼久才做出那些正常該有的反應?
是因為這該是場表演,所以他們深信自己是被規則保護起來的?
因為這是藝術,作為它的觀眾不應當去擾亂它?
只有做一個精神失常的人才有資格被允許去干擾藝術吧,就像之前對談活動上的患有妥瑞氏癥的吵鬧男人。
再聯想到在某種程度來說象征自由平等的美術館里,我們處處被規制的行為。
「看見地上那道線了嗎?
」「別靠太近了!
」「別伸手!
」還有那些暗處的約定,「乾乾淨淨的進美術館哦!
」「接受策展人的指揮移動吧!
」文明似乎意味著小心遵從「藝術」中人為設定的規則。
可是我們到底在期待些什麼呢?
這些「文明」之地,整個社會本不就是教導人類安安靜靜呆著別惹麻煩的地方嗎?
如果電影中表明「野人」藝術家打破表演與現實界限的行為也是他藝術的一部分,就像一些當代表演藝術作品或實驗劇場一樣,一切觀眾自發的反應都是作品的一部分,我大概會覺得作品帶來的爭議與過後的思考使得混亂或傷害變得有所意義的。
而后我想到,是否「藝術」作為那個被劃出的Square,在這其中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為人所推崇。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既定規則被違反或打破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呢?
人們總說,民主的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需要時刻被挑戰。
電影里的美術館便為賺取病毒式的關注在YouTube上發佈與理念相悖的宣傳短片。
類似這樣在當下的理解裡打著「言論自由」消費弱勢族群,目的不純的行為,它是否理應被質疑被割除。
我們會不會懷疑自己,懷疑我們所謂落後的思想限制了先進的目光。
人們又該如何劃定行為背後的意義和目的呢?
或者說,我們不應該習慣去揣測一個行為或是藝術家創作的動機?
美術館門前象征黑暗與無知的中世紀銅像轟然倒地,焊上一圈光亮的四方淺溝,方形之中是關愛與和平,人們沒有等級之分權利平等。
那麼方形之外呢?
4 ) 《魔方》里的三个当代艺术展,你看懂了么?
当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遭遇语境转移,当平权离开阶级的庇护……坍塌的不止是博物馆那个巨大的魔方。
距离上一次正经八百写影评已经好几年了,上周有幸参加平遥的首届国际电影节,八天里每天超过10个钟头坐在国际放映标准的影院里看4K乃至巨幕上的非商业片儿,彻底激起了我早已麻木的观影体验——要知道,自从若干次出现2D票必须换3D场的坑爹经历,我已经很久不进电影院。
这篇儿不是单纯的影评,出于喜爱,我想捋一下电影《魔方》中的三个艺术展和电影叙事的关系,毕竟,作为一个艺评人,总得有点儿专业态度。
【电影里的三个当代艺术展】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博物馆里的采访。
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博物馆馆长Christian,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其艺评文章里的拗口用词。
Christian解释半晌之后举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博物馆对于艺术品来说,就是全部的意义。
这段记者问不下去而Christian也并不想多说的开篇采访,把《魔方》这部电影划进艺术圈的步调。
作品A、景观装置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某位艺术家把自身用品或垃圾做了多年的积累后,重塑成型,并堆砌成景观类装置作品。
墙上的字是“YOU HAVE NOTHING””。
在电影里,这个作品从第一个镜头就被置为访谈的背景,中途多次出现游客参观、清洁工打扫的画面。
作品B、大猩猩(视频+行为艺术)说的是“大猩猩”,由人类扮演的大猩猩,展示野兽的自然习性——其实也是艺术家或者导演对“人类兽性”一面的某种暗示。
展览中的录像作品,也多次出现在主角独处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大猩猩”的扮演者是《猩球崛起》的动作指导,也是一个著名的研究猩猩的艺术家。
由他在本片饰演的“被艺术家豢养的类似大猩猩的人”,在高潮部分的表演,足以震撼荧屏内外。
作品C、魔方(方形)Christian策展的阿根廷艺术家的作品“魔方(The Square)”的作品理念是这样的:方块里是一个信任和关怀的场所,走进它的内部,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男主角带着两个女儿,在博物馆里参观尚未公开的展览《魔方》是贯穿电影始终、一直在包装宣传层面还未正式开放的重要展览,除了博物馆里的展厅部分,还有广场上的公共艺术作品。
为了“布展”也就是将“方块”安置在广场上,电影开篇推翻了一座中骑士形象的雕像作品。
显然,骑士雕像是一种英雄崇拜的指征,而“方块”的代替,则是打破个体异化,提倡人人平等。
换个说法,就是西方政治哲学里的“平权”意识。
“平权”的本意是帮助少数及弱势群体,消除歧视;但是瑞典原本就是一个高度平等的国家,为什么影片还要挑这样一个话题?
要知道,在很多国家,过分强调和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早已遭到多数人的逆反心理,也由此出现一个词汇:“逆向歧视”。
回看展览《魔方》,从策展角度来说,一个展览,一旦涉及到公共艺术,面对的就不仅是进入博物馆的那批观众,还需要各阶层、群体的关注,甚至全民参与和讨论。
当代艺术面对大众观看并不困难,毕竟,除了周一,博物馆每天都要开门,进门的人大部分都会参观所有展品;只是进门参观的人非常有限,当代艺术走出博物馆变成公共艺术,难在如何“引起关注”。
于是博物馆主动出击寻找宣传和包装的方案,试图把这个作品的开展,作为一个话题在社会上引爆。
展览《魔方》的室外部分你看,一个相信艺术品只有在博物馆里才有价值的馆长,竟然试图让展馆里的作品,走出博物馆获得全民关注。
然而,他的采访里并没说错,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影片开启失控模式。
【正 文】《魔方》是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参展影片里实力最强的一部,载誉“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既然是个电影,又是个国内上映遥遥无期的艺术片,那就索性用“艺术观看的角度”拆解一下剧情——就着那个艺术博物馆的背景和展览们。
《魔方》这个电影虽然有一条事件感很强的主线,却并非线性叙事。
尤其是,从第一个镜头起,就透着一股子并不想让人看懂的“当代艺术”范儿。
男主Christian影片主角Christian是瑞典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精英阶层、著名策展人,离异,开特斯拉。
影片说的是Christian在广场上被碰瓷团伙盗走手机钱包,费尽周折粗暴找回,最后想要弥补“错误方式”造成的恶果。
在这条主线上,身份和立场差异导致的人与人的不沟通、不信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日常“车祸”,而现代人社交恐惧的源头,在“车祸”中被镜头放大得纤毫毕现。
1、Christian上班路上在某广场遇到一个碰瓷团伙,当Christian面对未知威胁,在全员漠视的人潮中试图伸出援手时,“求助者”掳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
博物馆里,Christian的下属,一个年轻的黑人,对手机(开启了定位功能的苹果机)事件极其兴奋,主动跟踪定位,自告奋勇帮助Christian寻机。
而方案是,给某栋被定位的“贫民窟”群发打印的威胁邮件:小偷,你被定位了,到XX便利店交还手机和钱包,注明XX收。
Christian被这个荒唐的方案说服了,带着同事找到那栋大楼。
不料同事执意待在特斯拉里看车,Christian只得独自上楼发邮件。
上楼之前,Christian问他的同事,我还能相信你么?
Christian穿上同事的夹克去发邮件2、Christian请的外宣团队来博物馆开会商讨《魔方》的宣传方案。
值得一提是,一个画风奇特的老男人出现在会议上。
在Christian的团队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拎着一个吃奶嘴的婴儿一起上班和开会。
这个画面在电影里被多次强调。
没错,这是典型的自由、开放、平权的象征,还会让人艳羡艺术家的浪漫——“艺术家”的身份往往会掩盖一切不合理,就像在艺术馆里,面对金箔和废纸,我们会一视同仁。
婴儿的出现,让这群拥有艺术界绝对话语权的人,显得过分随意和家常——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决定了“马桶”或者“垃圾”是否放在聚光下被我们解读成艺术。
3、第一个和艺术有关的“车祸”是在接下来的展览开幕酒会上,Christian发表完激动人心的人演讲之后,请出大厨介绍菜品,可是并没有人想听,艺术界的高端宾客纷纷涌向餐厅。
茫然无措的厨师忽然大吼一声喝住人群,随即讲完菜品介绍。
为什么馆长站在这里侃侃而谈宾客都会驻足倾听,而厨师站在这里却被当做空气?
你看,即使是博物馆筛选出来的群体,也会出现无法倾听的尴尬。
博物馆内的权利意识在这里出现第一个车祸。
4、作品A的作者在博物馆的论坛区接受公开访谈,观众席中出现一个口吐侮辱性词汇的妥瑞氏症患者(不自主出声、怪叫),又是平权意识的左右,不仅没有人去劝阻或者把他带离现场,还有一群人帮腔解释病人的不自控,并要求大家理解以及假装没有听到。
这段长达五分钟的访谈现场,像极了行为艺术。
主持人、艺术家、观众,以及屏幕外的人,在一声声“表子、狗屎”的辱骂中,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沉默着。
道理上没毛病: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以及老弱病残孕,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包括在一个艺术殿堂里听一场论坛。
这是平权的基本。
但是为了照顾老弱病残孕,而牺牲掉的一部分人的权利,比如正常听讲座的权利,是否又违背了“平权”的基本概念呢?
博物馆里的第二场车祸,仿佛上一个车祸的高端版本,这一次,众宾客选择了忍耐。
——此处假装有截图—— 5、虽然发邮件那晚的经历极其不快,Christian的钱包和手机竟然完璧归赵。
极度欣喜的Christian在博物馆的派对上疯狂作乐,随后和那位采访过他的美国女记者回家。
在她的家里,极其荒诞的场景出现了:一只兀自走动,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坐在客厅里画画涂口红的黑猩猩。
关于猩猩这一段,隐喻的是男主在女记者家中看到了他的“本我”。
而他在本我暴露的同时,忽然有了遮羞的念头,也就是自我的回归——于是他的本我在涂口红,看报纸,慢慢变回一个理性的人……然而门一关,本我在性欲支配下又占上风。
魔方1_腾讯视频在“文明猩猩”的窥视下,Christian和女记者在床上做完兽欲大发的苟且之事,又因为争夺避孕套的处置生出另一波尴尬。
搞笑片段_腾讯视频6、Christian被奇怪的一夜情和便利店出现的第二个寄给他的“邮件”折磨得心神不定,没有心思讨论即将上线的宣传活动,草草打发给同事。
而这个讨论的决定是,给即将开展的《魔方》做一个和作品理念完全相悖的网络宣传,利用恐怖视频的效果在YouTube上赚取病毒式的传播和关注。
宣传的事情分给专门做策划的公司原本是个很正常的理念,毕竟术业有专攻——但是,这个展览关系到博物馆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的语境转换,作为策展人和馆长的Christian,明明非常了解“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却任由外宣公司重新包装“方块”并放在YouTube上——他们聘请的外宣公司,不过是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此处也算是个Bug)。
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7、展览A再次发生车祸,这次是真的。
有人来告诉馆长,他们的作品A被清扫车碰坏,需要联系保险公司;Christian立即阻止,要求同事不要声张,关闭展览,晚上按照片复原。
清扫车对Christian们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入这个让人安心的庇护所(另一种概念的魔方),他们的身份是稳定的,话语是有力的。
这种舒适感让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具——正如他们带着孩子去博物馆上班那样。
8、女记者到博物馆找到Christian,执意和他探讨那一晚(一夜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到女记者,Christian下意识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名人都会遇到的麻烦,比如勒索。
然而女记者只是告诉他,她觉得自己爱上他了。
显然,Christian并不相信。
就像Christian遇到作品A被损坏时做出的决定那样,面对女记者的逼问,他选择不承认、不沟通和不相信,试图把一夜情当做没发生过。
9、Christian收到的第二个便利店“邮件”来自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小男孩。
男孩因为群发的邮件被自己的父母当做小偷,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
男孩儿一再寻找Christian,希望Christian向父母澄清自己不是小偷,遭到Christian的拒绝。
Christian在家门口赶走了男孩儿,却被自己女儿的到访吓得不敢开门——一个堂堂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家里,竟然恐惧一个贫民窟的孩子。
他害怕什么?
10、这时,博物馆外聘的小视频组合做出来的宣传片儿在YouTube上火了。
外宣公司的宣传方案是,让一个五岁的金发小乞丐抱着布娃娃走进这个方块,并在这个方块里被炸得粉碎。
一件博物馆的艺术作品,竟然把乞丐、白人、儿童和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视频立刻激怒大众并引发病毒式传播。
影片的气氛随即到达高潮。
(这里解释一句:“金发白人+乞丐小女孩”作为恐袭目标的特征,触怒的是因为“逆向歧视”而早已憎恶“平权”的大多数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无产阶级。
)11、《魔方》的高潮部分是一个看似和主线无关的独立现场。
在博物馆的宴会上,作品B“大猩猩”的现场行为艺术……表演。
方形 片段2“大猩猩”入场之前,有声音对宾客提示:“这是一个假想的森林,会有危险发生,请大家按照森林法则求生”,众宾客仍然以为这仅仅是一个餐前真人秀的表演。
随着表演者的情绪调度,宴会现场逐渐失控,被冒犯的艺术家和一些宾客愤然离席。
“大猩猩”随即控制整个宴会,成为森林之王,紧张的情绪蔓延开,所有人噤若寒蝉……直到“大猩猩”几乎当众强奸女嘉宾,终于有人反应过来,爆发,一拥而上,暴打异类。
如果回忆起前文的猩猩,你会发现,上一只真的猩猩在两个疯狂苟且的人面前坐着画画;而这次的假猩猩,却在人类的高雅殿堂上兽性大发。
除了两个荒诞场景里“真假猩猩”的互喻,这一幕与之前的某些场景也颇为相似——被妥瑞氏症患者打断的艺术论坛。
那位妥瑞氏症患者和这个扮演大猩猩的人一样,都是周围这些“高雅艺术的欣赏者”害怕沟通的异类(少数裔)。
无法沟通,是因为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份过分维护,害怕任何当众行为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不尊重平权)。
与其说他们是害怕阶级对立,不如说是他们害怕自己变回对方的阶级(出现对方的举止)。
“大猩猩”用一个失控的表演,成功地把现场的“高雅人士”统统拉下文明的神坛,返回兽性的森林。
现场爆发一段众多礼服男围殴异端分子的“粗鄙行为”。
如果你看懂了这个行为艺术,这个电影里所有的“不合理”的存在就都有了解释——平权,的确存在于类似博物馆这样的高雅殿堂,也就是“魔方”之内,但是,当无法沟通的异类进入这个魔方,众人呈现的“集体失语”其实源于恐惧,也是他们在“魔方”之外,对他人或弱者选择视而不见、不听不信的那个恐惧——恐惧他们持有的文明、高端、正确的“标签”会被人碰掉。
12、失控的宴会之后,剧情从一开始的拒绝沟通,开始转向弥补性的沟通。
当Christian在家门口再次遇到贫民窟的男孩儿,他失手把孩子推下台阶,而这一切都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看在眼里。
终于,他去门外的垃圾堆翻找被扔掉的男孩的联系方式。
就像他按图复原自己的博物馆里的“垃圾堆”一样,这次他进入一个真正的垃圾堆,试图掩盖自己的过错。
找到电话号码,Christian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摄像头,录制了一段演讲般的措辞:对不起……我是犯了错,但这些错误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社会的错……你看,Christian们并不是放不下身段,而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根本就无法分开。
当他面对一个被他伤害过的小男孩,试图开口道歉时,却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几乎没说过人话——为自己辩护开脱以及向社会转嫁责任,是Christian们的惯性。
13、Christian在新闻发布会上道歉并宣布引咎辞职时,被愤怒的观众追问到哑口无言,还是油管视频组合的认责声明挽救了他。
随着记者对展览详情的追问,Christian顺势给《魔方》做了一把广告,尽心尽力地介绍《魔方》和艺术家的真正意图。
在Christian的官方发言中,一切仿佛又回到正轨。
你能说Christian是对艺术或者他人漠不关心的那类人么?
当然不是!
Christian们秉持环保理念,关心弱者,爱护孩子,对冷漠广场上对求助者施以援手……虽然他从未“忘我”,可是你看到了,他分明是以社会道德和身份职责为己任。
14、终于有一天,他带着孩子们路过那栋他群发过邮件的楼,带着孩子们一起上楼,敲开一家门,道歉。
独居的老人说,从未拆过没有收件人的邮件——而他们找的小男孩一家,上周就举家搬迁。
故事就这么结束。
Christian试图弥补的结局戛然而止。
【最后再说两句】在平遥电影节最后一天认真二刷的两个多小时里,我有一个钟头都在如坐针毡。
抛开《魔方》的剧情,就不难看见,影片中所有的失语和荒诞,都在直指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意识。
而当剧中人物真的忘记身份,传递出来的,又满目荒唐:比如Christian和街头乞丐的若干次沟通和互助。
是的,互助。
没有“情感投射”的互助行为,是影片中隐藏最深的真正“平权”意识——无论是求助方还是施助方,都是“你有钱,分我一份;你有时间,借我一点”的理所当然。
事实上,这种互助行为,通常发生在相熟的同事、朋友之间(同阶层),然而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精英和乞丐。
影片中所有突发情节,表面上是搞笑的包袱,镜头语言却是行为艺术的犀利。
就是那种,放大社会的荒诞、人性的不堪给你看,看到你不忍直视,艺术家却一直在演,导演也并不喊停……没有反转或者结局的提示,你甚至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然而面对巨大荧屏上的“真实”感,你却不得不一直反思,一直看。
比如这个影片里,长达五分钟的Christian楼上楼下的塞邮件;长达五分钟的艺术论坛上的侮辱性谩骂;长达五分钟的两个油管小男生的尴尬项目演示;长达五分钟的女记者对Christian的“事后”追责;长达十几分钟的“大猩猩”的宴会“表演”;长达十几分钟的记者发布会上的问责和解释……事实证明,该片的重复观看会对影片的人物设定产生生理不适。
这些全靠表情动作的单一场景、单独叙事的镜头,撕碎了电影的连贯性,也严重考验了观众的耐心……却渐渐显露出“行为艺术”的本质——唤醒。
回顾影片开头,Christian在广场上放置代表着信任和平等的“方块(The Square)”,又在广场(The Square)上被骗,这大约是导演玩儿弄的文字游戏——“平权”这个概念,在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早已被掏空本质,变成“失语、失信和互恐”的源头:少数人因此变得无所忌惮,更多的人都在尽可能收缩回自己的阶层(群体)里,无视他物。
这导致了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变得越来越差。
如果“平权”这个概念真的有用,唯一的出路已经在《魔方》中得到体验:变成TA。
无论你的肤色、信仰、种族、健康……是什么,你只需要变成你的交流对象,和TA处在同一个森林(方块)里,按照TA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语言、动作和思维方式和TA交流。
主动变成TA。
馆长说的没错。
你变不成TA(更好的),都是社会的错;而TA变不成你……那个惧怕十岁小男孩的博物馆馆长,你以为他怕什么?
他害怕男孩的家长有暴力倾向,害怕被不知底细的人勒索,害怕贫民窟的门内,住着一群向他伸手的人,就像他在便利店里遇到的乞丐。
当然,他更害怕的是男孩的出格举动让他受到非议,就像他会害怕黑人同事的不可信任,害怕美国女记者打扰自己的生活。
他所害怕的,和“社恐”人士所恐惧的其实一样——看不到你的底线,我没办法和你说话。
你以为只有博物馆馆长才会珍惜自己的名贵羽毛么?
其实,你我和他一样。
5 ) 虚伪的善意,空洞的形式
虚伪的善意,空洞的形式。
“‘方块’信任与关爱的圣所,在它之内,我们共享权利,同担义务”找到一种形式使人们之间互相信任和关爱,同时共享权利,分享义务。
这种形式可以被具现化为方块,也可以是三角形或者圆都可以,问题不在于为了展现形式而把形式艺术化,而是这种形式的具体内容和根据是什么,电影中的方块是完全空洞的。
仅仅为了形式而去形式化。
而且完全不符合现实,这不是乌托邦而是童话。
刚说这是信任与关爱的圣所,接下来就能看到路边的乞讨者和匆匆而过冷漠的人群。
就像主角的伪善,高谈阔论善与爱,却如此冷漠的对待乞讨者,讽刺的是当主角寻求帮助无人应答,只好去求助之前拒绝的乞讨者,电影多次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信任。
主角的艺术展完全是漂浮在云端的。
电影就是一点一点剥掉主角的伪善,他代表了大多数社会中的“文明人”。
开始主角用非常扰民切侮辱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目的。
还兴致勃勃的和下属构思这个计划,甚至于很快为自己找到了借口:我们是去执行正义的。
但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正义,无论抢劫者还是主角,无非是两方暴力的互相攻击,好像文明丝毫没有对这两个人产生影响。
不愿意承认自己仅仅因为肉欲而和偶遇的女性发生性关系,那个我室外路过的猩猩正如主角——他此时完全是个动物。
艺术展的作品缺失了,自己补妆上就好了。
能看出他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开头的采访也能看出,这里也很有趣,提问者和被问者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同时又心照不宣地认为找到了恰当的答案,维持了彼此的脸面。
电影展现的是人缺乏对他人的尊重,不再把他人同时作为目的本身,而仅仅是当做一个工具。
这正是电影的讽刺:“方块信任与关爱的圣所”确变成小女孩和小猫的葬身之地。
完全是为了流量和噱头,这就失去了其所要表达的内在价值,反而是站在了其反面。
道德成了金钱的妓女。
电影充满了有趣的讽刺,导演已经尽量把它拍着很温柔了。
我想伍迪艾伦会很喜欢这个电影。
6 ) 不喜欢《方形》的三点
1、生活化失效的尴尬对白由社交网络兴起的“尴尬”美学在电影中也常以场景化的形式出现,尴尬是人和人对话不对接所造成的隔空,本该作为生活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洪尚秀电影的对白以及去年的《托尼厄德曼》都通过电影传达出这种尴尬的氛围,实质是对生活的贴近。
而《方形》的尴尬则来自导演刻意制造的笑料,比如抽动秽语症打断对话这里,这样的尴尬场景作为导演一手调制的埋梗,如果观众不能发笑那么就会真的很尴尬,尤其在《百年酒馆》我已经提前看过这样的桥段,相反在那样的情景喜剧中反而更有一种生活化,这是因为场景的效力和连续性。
2、相关事件的散乱插入整个《方形》散乱的让人糟心丝毫没有表达清楚任何一点导演想要陈列的意象,只是一个个单一事件在毫无联系的推动着这个中产阶级人物的困境。
尤其冲突点廉价的像冷笑话。
3、怎样有效的讽刺中产阶级?
导演连着两部已经让人看出是和中产阶级杠上了,可是,不是谁都可以拍出布努埃尔那样的讽刺电影,例如《白日美人》的贵妇变娼妇的荒诞以及《资产阶级审慎魅力》的超现实和调侃把中产阶级孤立成一个切面去解剖他的精神实体。
而方形从现代艺术视觉切入中产阶级的精神世界本来是很好的,很贴切21世纪潮流的,因为随着物质的高产,现代艺术在降级甚至附带商品属性,从部分艺术的聚众性能看出现代中产阶级的新虚伪面貌和跟风性,但是鲁本太焦躁了一个个刻意的插入不仅不高明还把这样的嘲讽反变成自己的画蛇添足,尤其高潮戏猩猩晚宴处处透露下导演洋洋得意的自恋。
讽刺力度在直曝下不再有任何趣味。
所以总结方形,他既没有完成对现代艺术的批判,也没能和《游客》一样单一的吐槽中产阶级,更是漫不经心的提及些社会性话题。
综上融合了一盘散沙的电影。
7 ) 看不懂的电影hhh
挺少看这样镜头语言比较深刻的电影,全片的故事是支离破碎的,被分割成很多块,不同故事的碎块又相互衔接在一起,前一个多小时我都没有理解这个电影在讲什么;再加上没有仔细分辨每一个人的长相,就有些“这个人是谁?
他怎么突然出现的?
”等等疑问。
直到看到最后,才慢慢将故事拼成完整的,博物馆馆长想要宣扬“平权”,馆长为了找到偷自己东西的小偷给每一户人家都塞上了信封,馆长终于道歉了,向社会和那个小男孩,虽然小男孩搬家了。
有好几个物反复出现,一个是方形,电影开头就是工人在博物馆门口凿了个方形,哗众取宠的视频里女孩子走进一个方形,后面透过一个方形的玻璃窗。
看了几个影评结合电影后才稍微理解,这个方形是禁锢也是平权的发声。
一个是大猩猩,先是馆长跟女孩子回家后在家里看到看报纸的大猩猩,后来是在大厅内模仿大猩猩的人模仿失控扑向一个女孩。
真猩猩人模人样,假猩猩猩模猩样,反差好像是一种反讽。
一个是楼梯,有两个镜头的运镜一样,男孩一直坚持找馆长为自己澄清时画面是黑暗的,最后馆长主动去找男孩时画面是明亮的,自下而上上升的镜头好像在说馆长的善良的一面逐渐显现。
以及那三个展览没有怎么看懂。
第一个是开头的采访;第二个是好几个小山堆,旁边有一行字“you have nothing”(如果没记错的话),比较搞笑的是清洁工开着清洁车不小心破坏掉这个作品时,我以为是作者故意安排的;第三个就是选择“trust”还是“distrust”后进入到那个模仿大猩猩的人的照片的厅里,以及前方摆着的方形。
阅片量与理解能力有待提高。
8 ) 《方形》:关于策展的一切
当代艺术引发的非议,或者其本质问题,已经在《方形》这部电影中得到了全面展现。
之所以产生问题,其原因与“大众艺术”这个词汇中直露的悖论如出一辙。
当代艺术其实也已经将自己变为“大众艺术”,但不是像电影那般通过商业达致的普及,而是在姿态上变得更加民主:比方说装置艺术,便是邀请观众一同进行体验。
艺术不再有门槛之限,它敞向所有人。
当代艺术从自身缘发出了这种民主化倾向,但与此同时,它也仍然不忘记自己还是一门“艺术”,即一种加工、制造并进行包装的非消费品。
它建构在艺术内部的话语与规则之上,逾越了日常生活的界限。
这是当代艺术既敞开身姿接纳看众,同时又让他们觉得难懂的原因。
当代艺术在显现出民主社会共有的平等观念时,也不能忘记自己首先是作为艺术存在的。
展览简介-观众这种矛盾反映在了《方形》中,电影一开头就是女记者采访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场景。
面对出现在美术馆官方网站上的展览介绍,满脸疑惑的女记者想向克里斯蒂安探个究竟,却没想到收到的回复竟然如此简单:一件日用品放在美术馆中,是否也能成为艺术?
在此,尴尬或者说幽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克里斯蒂安直接但同时又有点无奈地指出了展览简介“不说人话”的事实。
这难道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看展活动中,都能明显感觉到的吗?
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似乎共用着一套与日常用语迥异的话语体系。
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能在展览的前言中读懂展览信息,更多情况是被淹没在高大上的术语中,有时还会有不少理论话语来帮忙。
前言原本用来帮助观者理解展览,最后让人感到更加困惑,说明它只有一个目的:即将作品包装为“艺术”,超越常人的理解。
当然,也有一些真诚的前言确实点中了展览的要点,但大多数都只为显示自己的“高级”,故而不想说人话。
艺术难道不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伪装起来的吗?
首先组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必须包括艺术家、评论家、还有有钱的买家,艺术家负责生产作品,评论家吹捧,买家购买,艺术就在三方组成的封闭圈子里流转。
并没有观众什么事,最后等到某位艺术家被吹捧起来了(以作品卖价衡量),观众便顺理成章地加入进来。
名气源自内部炒作,与观众无关。
艺术家-观众《方形》以逗趣的方式戳穿了艺术活动的这些“阴谋”,其中并没有高高在上的得意姿态,不如说姿态贵显真诚。
比如在展现当代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奇怪的关系上,《方形》再次采用了当面交流。
艺术家与主持人安坐在台上,观众静静待在台下聆听。
内着工装、外套西装的打扮,显示出艺术家虚伪的本性。
谈话情形也极为常见,对谈内容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艺术家的回答必须使用一台解码机器才能解析。
而观众却傻乎乎地坐在台下做好涨姿势的准备,但很可能对谈结束之后他们什么也没获得。
这还只是复制现实生活中艺术对谈的表面现象,更加妙趣的是台下一位观众因为病症不断地喊出不堪入耳的粗话。
这既是一个象征,代表着观众内心被压抑的不解和愤怒开始爆发出来——因为没有人会说自己完全看不懂当代艺术,而事实是他真的很可能完全没懂,而为了伪装自己有一定的艺术修养,他现在选择乖乖地坐在台下聆听发言,并装作听懂的样子——困惑和不解这个真实情况被压抑在潜意识里。
这些辱骂是对观众内心的病症学诊断。
同时这也将整个访谈现场变为一处艺术现场,因为它逾越了现实世界运作的规则,引人进入在场的情境中,并目睹自己身上涌现出的尴尬。
在如此严肃的艺术访谈中,观众应当约定不发出任何声音才是,除非是想提问。
但现在,这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被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交流遂变成一次艺术行为,所有人都卷入艺术运作的场域里。
这是整个场景引人发笑的原因:艺术家虚伪的话语被揭穿,艺术活动假造的姿态被拉低,艺术被嘲讽、被戏谑。
作品-策展人反映策展人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方形》中有两处。
其中一处是某件艺术品堆积的碎石不小心被参观者踢掉,面对如此严重的一件事情,克里斯蒂安“急中生智”直接指示工作人员重新将其堆好。
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是当着女记者的面作出这些指示的。
可能因为女记者不懂瑞典语因而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情况也很可能相反。
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事件引发的就是作品的归属问题。
如果作品被破坏后,策展人能在不告知艺术家的情况下自己将其修复,那么这件艺术品还能不能算是这位艺术家个人的作品?
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策展人或美术馆方面并没有权力来将因为观众不小心破坏的展品自行修复,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当然,因为这只是一件堆积作品,其完成也很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做的,修复前后也基本上看不出本质差别。
但因为非艺术家的外力作用在了艺术品上,那么它恐怕就不能再算是一件个人作品。
这也许就是艺术圈中众所周知的谎言,克里斯蒂安显然“驾轻就熟”,对于这种突发事件懂得如何处理;而《方形》揭开的只是其中一角。
这组镜头之所以让人感到尴尬、有趣,并引发了一丝丝难解,在于克里斯蒂安是当在女记者的面做出指示的,当时两人可正在计较性与爱的问题呢——撇开这个厚重又深刻的话题吧,虽然它很能揭示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虚伪本性——只谈指示的毫不遮掩,很可能说明了美术馆自行修复作品的举动在艺术圈中乃是司空见怪的事情,即便艺术家知道了又怎样,还不如省点事更好。
这从侧面透露出被蒙骗的只是观众,而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记者等无非沆瀣一气。
作品-观众当然,观众也不是蠢蛋,他们以自己的“无知”抗拒着艺术作品的“高深”。
这反映在电影中出现的几处对展览现场的观察。
作品旁边毫无例外地坐着傻乎乎的工作人员,监督看展的观众不去破坏展品。
然后观众一律带着无知的神情从墙壁后面探出头来,偷偷瞟了一眼便匆匆离去。
或者随身挂着相机的观众进到展览现场,呆立在那里,随便瞄上几眼,拍下几张照片,然后赶往下一处展览现场。
观众自然是看不懂的,但他们也不想看懂,他们展示着自己的“无知”,撕下艺术圈道貌岸然的伪饰姿态。
这个场景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它们是如此的熟悉。
在平时的看展过程中,不是经常看到类似的情形吗?
走马观花的游客打卡一般流转在一个个展厅,而对作品有多少具体的欣赏价值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
或者我们自己也不是这样吗?
即便带着一种审美的心态,但对当代艺术过于高深的理念感到蒙逼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匆匆瞄几眼,甩头走人吗?
如果说当代艺术将观众隔绝在外面,以内部圈子的方式运作,那么它同时也不得不“邀请”观众,来伪装自己确实是在进行艺术展览,虽然观众在此是以虚拟的方式存在的。
与此同时,观众也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艺术作品,比如将其当作拍照的背景或抬高生活品位的工具。
原先是艺术家通过作品与观众进行交流,如今则是作品将艺术家和观众隔绝了开来。
这就是当代艺术虚伪的内核,艺术成为了上层阶级自我话语的建构,大众只是被利用来为它的“民主化”阴谋服务。
作品-世界反映在作品-世界这一轴线的,是美术馆对展览作品的宣传,这同样也可以看成是策展人-作品轴线,但我们放在这里讨论。
《方形》中作品宣传的话题,是电影中尤其重要的一块。
因为只考虑流量,“病毒式传播”的宣传引发了伦理争议。
在这里,电影再次逾越出中产阶级的话语范域,将克里斯蒂安拖入了尴尬的境地。
这当然是为了再次凸显中产阶级道貌岸然的形象,同时也在嘲讽现代社会只看流量的宣传方式。
一切都是话题,与艺术作品了无关系。
并不是艺术作品吸引观众来看展了,而是外在于它的宣传吸引了大量观众。
这难道还不虚伪吗?
还不本末倒置吗?
如果说连当代艺术(号称最标新立异)都要病毒式宣传来吸引观众的话,那么其他的展览怎样才能保持人气?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反映在“作品-世界”这轴的,还有就是如果作品中的人物侵入了现实,会发生什么?
这也许是《方形》全片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原本只出现在展览屏幕上的奥列格如今化身为一具怒吼的猩猩出现在晚宴上,这是艺术侵入到了现实,虚构与真实并置在了一起。
现实生活的晚宴于是变成了一次行为艺术的展览现场:大家都以为只是来助兴的表演最终竟然发展为一场闹剧,震惊不已的中产阶级人士们还想在危急时刻保持住自己的体面(以那位艺术家为例),实在让人哑然失笑。
这涉及到了如何看待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9 ) 政治正确年代的“道德焦虑电影”:《广场》与鲁本·奥斯特伦德的电影创作
本文发表于《当代电影》2017年第7期。
转载请联系公众号“当代电影杂志”提要:本文在回顾201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得者鲁本·奥斯特伦德的创作历程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他的获奖影片《广场》中的艺术手法与社会内涵。
文章着重探讨了他在影片中对当代艺术及其观念的创造性使用,分析他是如何在剧情、结构和主题层面设置多重的互文关系,并探讨他电影中的社会批判指向。
关键词:当代艺术 旁观者效应 政治正确 鲁本·奥斯特伦德 戛纳电影节2017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迎来70周年大庆,备受瞩目的“镶钻金棕榈”最终被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凭借其第五部长片作品《广场》获得。
首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奥斯特伦德事实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戛纳系导演”——他的第二部长片《身不由己》和第四部长片《游客》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并凭借后者获得当年“一种关注”评委会奖,其第三部长片《游戏》也入围了“导演双周”单元。
自《游客》声名鹊起之后,奥斯特伦德的职业生涯可谓是坐火箭般上升,压哨入选主竞赛单元的《广场》获得了评委会和媒体的一致好评。
凭借自己鲜明的作者风格和作品中尖锐的社会议题,金棕榈加身的奥斯特伦德已经足以跻身当今最重要的艺术电影导演之列。
鲁本·奥斯特伦德和镶钻金棕榈回顾奥斯特伦德的电影创作,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普通人在面对窘迫情境时的道德问题,此外多数作品还有着对瑞典社会中“政治正确”的辛辣嘲讽和深刻反思。
目前中文世界对奥斯特伦德的研究文章仅有台湾影评人李达义的《鲁本奥斯伦:社会现象实验室》([1])一篇。
英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游戏》一片的全面详细探讨上,包括Ingrid Stigsdotter([2])、Helena Karlsson([3])、Elisabeth Stubberud与Priscilla Ringrose([4])、Anna Westerståhl Stenport与Garrett Traylor([5])、Christian Gullette([6])与Amanda Doxtater([7])的文章。
学者们着重分析的是《游戏》中引发激烈辩论的种族和阶级议题,并且均注意到了奥斯特伦德作品中独特的视听语言风格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在对奥斯特伦德作品作者风格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广场》一片的艺术手法与社会内涵。
作者风格的形成与变化:长镜头、蒙太奇结构与道德议题奥斯特伦德的创作以《游客》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的主要艺术手法是以固定机位长镜头为主,结合摇移与变焦调度,以实现镜头内部的蒙太奇效果。
其中全景长镜头数量很多,近乎一场一镜;同时他大量使用非常规构图,基本不采用连贯性剪辑,并通过对声音和画框的强调来展示画外空间;此外,严格不使用配乐。
这种视听语言体系受到了瑞典电影大师罗伊·安德森的深刻影响,如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金熊奖的《银行事件》,全片仅有一个长达近10分钟的监视器机位的长镜头构成,在极端的“真实时间”中,通过变焦和摇来形成镜头内部的蒙太奇。
同时,他在影片结构上的特点是采用多线平行的蒙太奇,通过对多组人物的描写形成一种对“普遍性”的展示,从而表达一种与他的镜头调度类似的评论性的观点。
其长片处女作《吉他蒙古人》和第二部长片《身不由己》均采用相同的结构,前者通过有着相互微弱关联的数组人物来展示“人类难以被他人理解的行为”,后者则是五组完全不相干的人物在遭遇到“面子问题”时承受到的道德压力,以及他们不同的应对方法。
这种结构近似于罗伯特·奥特曼的名作《人生交叉点》(Short Cuts,1993),也有影评称他的这些作品是由一系列“尴尬的片段”(awkward vignettes)组成的([8])。
到了影片《游戏》中,这种结构则变化为较为连贯的主线情节与两组插叙性的、有着微弱关联的支线。
《游客》与《广场》可视为奥斯特伦德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这两部作品不再强调(全景)长镜头,同时构图开始常规化,也开始使用常规的剪辑方法,包括视线匹配剪辑等等,但擅用画外空间的特点得以保留;同时叙事也变得较为集中,均围绕着一位主要的叙事人展开,不再采用平行蒙太奇结构。
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两部影片都使用了音画平行的、评论性很强的配乐:《游客》中用于渲染不安气氛和指称危机的《四季·夏》,以及《广场》中具有调侃性的无伴奏合唱。
这种视听风格和剧作结构上向常规电影的转变,让奥斯特伦德获得了巨大成功。
奥斯特伦德在影片主题上的标志性特点是探讨道德问题。
从《身不由己》开始,个人在面对群体时的“面子问题”与“道德压力”就成为了奥斯特伦德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共同困境。
如《身不由己》中有在生日会上被烟花炸伤却坚持不去医院的男主人、不敢承认弄坏了大巴厕所上窗帘的女演员、迫于同学压力不敢坚持自己意见的女生,《游戏》中被几个黑人少年霸凌的三名少年,《游客》中不愿承认自己面对雪崩不顾妻子和孩子而独自逃生的丈夫等等。
而同时,这些作品又通过这种困境来提出社会问题,如《身不由己》中的“责任分散”,《游戏》中的移民问题与政治正确导致的“反向歧视”和“双重标准”,以及《游客》中的群体无意识等等;同时贯穿性的一个表述则是个人主义至上而造成的人情冷漠。
其中以《游戏》中提出的黑人移民少年犯罪问题最为尖锐,奥斯特伦德在影片中完成的表述是瑞典主流社会基于“政治正确”的一味纵容造成了这种恶果。
影片在瑞典引发了轩然大波。
([9])这也是促使奥斯特伦德在接下来的作品中转型的直接原因。
作为“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广场》及其艺术手法《广场》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是将当代艺术同时呈现为影片剧情、结构和主题的要素。
实际上影片的片名“The Square”就是片中一件当代艺术装置作品,由一个放置在(虚构的)皇家博物馆(X-Royal Museum,以瑞典皇宫为原型设计)门前广场上,LED灯管围成的方块构成;这个装置同时也有一个放置在博物馆内的版本。
其概念是“The Square(方块/广场([10]))是信任和关心的一处圣地。
在其中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件装置艺术作品是导演本人于2015年创作的,于瑞典韦纳穆市(Värnamo)首次展出;影片中则伪托在一位阿根廷的女艺术家和社会学家名下。
这件装置主要在于探讨社会学中的“旁观者效应”,艺术家希望以此来检验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选择信任他人的观众可以将手机、钱包等物品放置在装置中并离开。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韦纳穆市的“The Square”被居民开发出了其他的功能:青少年的夜间接头地点、情侣求婚的场所和残疾人乞讨的场所([11])——总之跟这件装置的主旨完全无关。
这一细节也被导演用在了《广场》这部影片中。
The Squre户外装置影片的主人公克里斯蒂安是皇家博物馆的策展人,他看似完美的生活从一个早晨开始逐步陷入泥潭:首先是他因为试图帮助一个在广场上呼救的女人,因而被她的同伙偷走了手机和钱包。
他为了找回财物,向一整栋楼的居民家中投放了指控他们是小偷的匿名信,虽然拿回了手机和钱包,但也因此遭到了一名愤怒的少年的抗议和纠缠。
他与一位美国女记者在派对后发生了一夜情,之后却被女记者指责。
他策展的装置艺术作品“The Square”因为宣传团队的病毒营销视频而陷入舆论危机,甚至被迫辞职……影片的结尾他终于放下架子挨家挨户去向被他投放过信件的居民们道歉,却发现无法找到那位愤怒的少年……“The Square”作为与片名相同的当代艺术作品,起到了异常重要的结构性作用。
影片的开场段落中,为了要在皇家博物馆广场安装这件装置,需要移除一尊青铜塑像;而看似稳妥的吊车绳索实际上并不能承受塑像的重量,刚刚从底座上移开,塑像就轰然倒塌,摔得四分五裂。
这一颇为嘲讽的段落实际上构成了影片的预叙:克里斯蒂安的生活也是如此忽然地陷入了麻烦。
“The Square”通过“旁观者效应”对人类之间信任的考验在影片剧作中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克里斯蒂安的手机与钱包被窃,正是因为他在广场上众多“旁观者”中(并不心甘情愿地)站了出来表示善意和信任,因此中招;而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停下脚步,第一次他(在广场上)茫然无助,第二次他(在商场里)发现只能求助一个乞丐;他信任了手下提出的寻找财物的方案(手下却在关键时刻成了“旁观者”),因此惹来了麻烦;他大女儿的啦啦队表演也在“团队效应”的层面探讨着信任问题。
在他带着两个女儿去参观博物馆中展品的时候,选择“信任他人”的两个女儿竟然都不敢将手机放在“The Square”装置之中(这个装置的室内版本甚至还没有开放公众展览,换言之,展厅内除了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其他人)。
此外,克里斯蒂安在丢失财物当夜去散发匿名信的时候,画面中俯拍的居民楼楼梯间,恰好形成一个正方形的发光区域;这个段落不仅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探讨有关“信任”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在视觉上形成了与“The Square”的呼应关系。
The Square室内装置影片中提及的当代艺术作品还有名为“You have nothing”的石子堆装置作品,一度被清洁工破坏(当代艺术博物馆常有的笑话……);一堆由诸多椅子堆叠起来,规律地发出倒塌的巨响的装置作品,成为女记者在一夜情之后继续纠缠克里斯蒂安的场景的后景,极好地创造了尴尬气氛并形成了某种比喻关系;最后则是影片中十分重要的录像—表演作品“大猩猩”。
在皇家博物馆中展出的录像作品中,好莱坞动作指导泰瑞·诺塔里(Terry Notary)扮演的艺术家奥列格在纯白的背景前赤裸身体,直视镜头模仿大猩猩的表情,这件作品也成为克里斯蒂安几次独处时刻的后景;此外在一场答谢赞助人的晚宴上,应邀表演的奥列格惟妙惟肖的表演逐渐失去控制,并因为对一位女宾的“冒犯”而引发混乱场面——这场意在引用布努埃尔《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1972)的宴会场景无疑是影片中最为精彩的段落,并事实上也构成了对全片故事的提喻。
更为有趣的是,克里斯蒂安在与美国女记者约会的时候,发现她与一只黑猩猩共同生活,而这只黑猩猩的爱好竟然是绘画——这一颇为讽刺的细节(黑猩猩作画与人类做爱的对比关系)又与(人类扮演的)“大猩猩”这一作品形成了互文关系。
You have nothing
背景那堆椅子特别之令人焦虑《广场》中当代艺术的用途并不仅限于作品层面,奥斯特伦德将当代艺术的观念或者“话语”与剧作结合起来,形成了影片最具创造性的手法。
影片开场段落就是克里斯蒂安接受美国女记者的访谈。
女记者引用了一大段克里斯蒂安关于“展览/非展览”的佶屈聱牙的论述并请他解释。
事实上克里斯蒂安也并不能清晰地解释,于是他(事实上)引用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去解释这个概念,指出当代艺术最核心的要素事实上是博物馆空间。
上一段所述的几件作品均在不同层面阐释这一观念,如“大猩猩”的表演引发的灾难性事件正是因为脱离了博物馆空间;而“The Square”的病毒营销视频事件也是如此,宣传团队制作的视频短片是在“The Square”的室外装置中“炸毁”了一个金发碧眼的乞丐小女孩,从而引发了舆论危机(当然这个段落导演还意在探讨媒介对人的异化作用([12]))。
克里斯蒂安在被迫辞职的记者会上被记者们挖苦和攻击,但中途应馆长要求念了公关团队的稿件之后,不无嘲讽或者令人惊奇地,所有的记者忽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件即将向公众开放的展品,于是克里斯蒂安驾轻就熟地开始使用他那套当代艺术的话语来向记者们介绍那位“阿根廷的女艺术家/社会学家”。
换言之,如果那部引发舆论危机的视频是为了阐释某种“艺术观念”,那它当然是合理合法的,甚至需要被严肃认真地讨论和予以正面评价的。
录像作品“大猩猩”这一戏剧性的转折恰好也与宴会上“大猩猩”的表演形成互文关系:尽管所有的人都在一个扮演大猩猩的“艺术家”的表演中感觉到尴尬、难堪、不适、被冒犯,但因为“这是艺术”,所以每位来宾必须正襟危坐地“欣赏”,或者说作为“旁观者”,直到忍无可忍。
导演在影片中还安排了一个类似的场景来解释:艺术家朱利安的访谈会现场被一名患有“秽语症”的观众不停干扰,但无论是朱利安还是主持人或是现场其他观众(作为“旁观者”)必须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便这名观众的言辞完全不堪入耳——因为作为有着良好教养的中产阶级,必须以最大的宽容“尊重弱者参与艺术活动的权利”。
而极为讽刺的是,同样是皇家博物馆的观众,在面对丰盛的自助餐时,完全没有耐心听厨师介绍菜品,并且唯恐自己抢不到食物——所以最终奥斯特伦德完成的是这样一种复杂的表述:正如装置作品“The Square”试图揭示的那样,“旁观者效应”会极大地考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与当代艺术的话语一样,政治正确同样是一种基于“旁观者效应”而导致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的状态。
阶级还是种族?
讽刺与批判的指向与结构严整近乎舞台剧的《游客》不同,《广场》又回到了某种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克里斯蒂安的工作、生活、家庭(离异,与前妻生有两个女儿)几条线上逐渐陷入麻烦是交织进行的。
作为一名当代艺术策展人,克里斯蒂安的生活十分优渥,衣着时尚,用着最新款的iPhone手机,开着特斯拉轿车,住在高档公寓之中。
偷走他钱包的两个人则住在郊区的一栋普通公寓中,显然是个问题社区——克里斯蒂安去投递信件的时候甚至不敢穿西装,而他的特斯拉轿车也引起了(大约是小混混)的好奇。
前来纠缠他、要求他道歉的那名少年,从衣着到教养显然都是来自底层阶级。
奥斯特伦德采用这种显而易见的阶级话语,却未曾分析其背后结构性的因素;结合他的创作历程和对《广场》的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他采用了精心修饰的阶级话语来取代种族话语。
在导演阐释([13])中,奥斯特伦德称此片的类型为“讽刺剧”(satire),影片的主角克里斯蒂安是一个极为安全的被讽刺对象:白人、男人、健康人、中产阶级精英,对他的讽刺包括:1)自恋:自认为是“公众人物”而不愿意去问题社区散发匿名信,跟一夜情对象争抢用过的避孕套;2)自负:拒绝向受到家长怀疑的少年道歉,还在争执中失手将他推下楼梯——后一个不仅堪称“凶残”,而且还是逃避责任;3)大男子主义:对一夜情对象睡过就忘;4)装腔作势、推卸责任:好不容易下决心向少年道歉,结果张嘴就是分析社会问题的“当代艺术策展人话语”;等等。
对他的惩罚无非也就是让他在大雨夜去翻垃圾箱,以及丢了工作;但问题在于,即便如此,他生活中的种种麻烦,并不是他的性格造成的,而是意外的事件——因为相信了陌生人而丢了手机钱包,因为相信了手下的建议去散发威胁信而惹来了麻烦,因为急于找回财物和应对少年的纠缠而没有耐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也没有去审核视频,导致后面的公关危机。
重要的是,丢工作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的错误而是因为不可理喻的“政治正确”;并且他也有意悔改,最后也获得了奖励——两个女儿由衷的认可。
所以在影片中,克里斯蒂安的困境来自一系列偶然性(正如《游客》中的雪崩),他的性格只是将其逐步加深;他本人并没有根本性的责任。
那么问题来自哪里呢?
自然是社会,但又并不能说是社会。
因为影片主要探讨的就是“旁观者效应”造成的责任分散。
影片中有两处提示非常重要。
其一是在制作视频的时候宣传团队就已经预料到可能的问题,主动选择了乞讨者的外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典型的瑞典人长相的小女孩”,这显然是在规避如果使用其他族裔的乞讨者可能引发的问题,是典型的因为政治正确而造成的自我审查;但在记者会上,第一个站起来指责克里斯蒂安的记者的论点就是“你为什么攻击乞丐这个如此脆弱的(vulnerable)群体?
”这一点需要联系到《游戏》一片的结尾场景:一名白人家长替自己的孩子向一名黑人少年讨还被抢劫的手机,黑人少年大声尖叫引来路人围观,充满“正义感”的路人却因此指责白人家长“攻击脆弱的移民群体”,“他们不像你的孩子那样有许多机会”。
《游戏》一片受到的指责显然极大地刺激到了奥斯特伦德(《广场》中克里斯蒂安在记者会上的辩白其实不无导演自况之意),使得他彻底规避了移民(当然,绝对不能提的还有难民)群体。
围观特斯拉的那群小混混听口音极有可能是移民,但他们甚至没有出现在画面里;更有趣的是,影片中的乞丐竟然都是白人,连患有秽语症的那个观众都是白人(男人)。
另一个提示则是“大猩猩”的表演。
且不说“猩猩”是极为常见的种族主义话语,且看那场晚宴上发生的事情:无论这是什么当代艺术作品,但在宾客或者观众看来,是一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只有兽性的人,他/它不懂规矩,冒犯了在座的教养良好的宾客;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它最后侵犯了一名女性,开始撕扯她的衣服。
这也是在座的众多男士忍无可忍的直接原因,所以他们群起而攻之,狠狠殴打了他/它。
那么这显然是颇具社会问题的移民,更恰当地说是难民的隐喻(尤其是联系到瑞典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
在这里导演终于将当代艺术话语与政治正确直接联系起来,并通过这种“想象性的解决”提供了一种仪式性的胜利。
结语:过载的文本与“道德焦虑”《广场》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文本的过载状态,正如影评人“元首的秘书”所言:“更像是一次统合人类行为的疯狂实验,因为奥斯特伦德几乎为每一个场景分离出两到三层含义,这就让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难以想象的庞大,甚至有一种过度填鸭的感觉。
”([14])奥斯特伦德成功地将当代艺术从作品到观念融入影片的大部分场景,并有着明确的表达。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当代艺术话语与“政治正确”的话语在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通过“旁观者效应”联系了起来。
无怪评委会主席阿尔莫多瓦称赞这部影片“着眼于政治正确的独裁性,并提供了许多例证”([15])。
而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对政治正确的批判,恰恰与冷战年代的波兰“道德焦虑电影”有着结构性的相似:用道德问题来揭示对某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巨大的不信任;同时,焦虑之处在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必然有一天会随着社会巨变而走向终结,但并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不过奥斯特伦德总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在这部影片中精明地选择了一个在“政治正确”意义上最为安全的对象,并使用了讽刺喜剧的手法,让这部其实议题极为尖锐的影片变得轻松有趣。
但必须看到,导演对克里斯蒂安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嘲讽而并不是批判,他的困境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困境而只是尴尬处境。
正如最后那次没能完成的道歉一样,奥斯特伦德实际上指出,在当今这种社会环境中,(阶级与种族间的)和解根本不可能发生;而无视社会问题的实质并一味自我反省、搞政治正确(“受害者先道歉”),只会越陷越深。
而到那个时候,恐怕谁都笑不出来。
附:鲁本·奥斯特伦德年表1974年 4月13日出生瑞典哥德堡大区斯蒂尔斯岛(Styrsö)2001年,毕业于哥德堡大学电影导演系2002年,创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平台电影”(Plattform Produktion)2004年,编导故事长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获第2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影评人奖。
2005年,编导短片《自传场景6882号》(Scen nr: 6882 ur mitt liv),获欧洲电影奖最佳短片提名。
2008年,编导故事长片《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又译作《五道人生难题》),入围第6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获马德普拉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2010年,编导短片《银行事件》(Händelse vid bank),获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金熊奖;另获欧洲电影奖最佳短片提名。
2011年,编导故事长片《游戏》(Play),获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Séance "Coup de coeur"奖;另获第24届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14年,编导故事长片《游客》(Turist,又译作《不可抗力》),获第6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评委会奖,另获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提名,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短名单(前9位)。
同年9月被哥德堡大学Valand艺术学院聘为电影系兼职教授。
2015年,美国林肯中心电影协会为其举行题目为“IN CASE OF NO EMERGENCY”的个人作品回顾展。
2016年,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评委。
2017年,编导故事长片《广场》(The Square,又译作《自由广场》),获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他的其余作品还包括滑雪视频作品《上瘾》(Addicted,1993)和《自由激进分子》系列(Free Radicals 1&2, 1997&1998)、纪录短片《让别人去爱》(Låt dom andra sköta kärleken,2001)、纪录片《再次成为家庭》(Familj igen,2002)、短片《夜泳》(Nattbad,2006)等。
奥斯特伦德还多次获得瑞典电影金甲虫奖(Guldbagge Awards)的各项奖项和提名。
[1] 载台北电影节统筹部、涂翔文主编《瑞典电影》,新锐文创,2012年7月,第169—177页。
[2] ‘When to push stop or play’: The Swedish reception of Ruben Östlund’s Play (2011),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3, Volume 3 Number 1, pp41-48.[3] Ruben Östlund’s Play (2011): Race and segregation in ‘good’ liberal Sweden,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4, Volume 4 Number 1, pp43-60.[4] Speaking images, race-less words: Play and the absence of race in contemporary Scandinavia. ibid, pp61-76[5] Playing with art cinema? Digitality constructs in Ruben Östlund’s Play, ibid, pp77-84.[6] Are our malls safe? Race and neoliberal discourse in Ruben Östlund’s Play, Journal of Scandinavian Cinema [J]. 2016, Volume 6 Number 1, pp25-73.[7] From Diversity to Precarity: Reading Childhood in Ruben Östlund’s Film, Play (2011). New Dimensions of Diversity in Nordic Culture and Society[M]. Eds. Jenny Björklund and Ursula Lindqvist.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6. pp190-208.[8] Matthew Blevins, In Case of No Emergency: The Films of Ruben Östlund: The Guitar Mongoloid Review. [EB/OL].(2015.04.04)[2017.06.12]http://nextprojection.com/2015/04/06/case-no-emergency-films-ruben-ostlund-guitar-mongoloid-review/ [9] 见2。
[10] 鲁本·奥斯特伦德对此作品的阐释是“一个放置在城市广场上的物理的方块”(a physical square placed in the town square)。
见The Squre, Press kit. [EB/OL].[2017.06.12] http://www.festival-cannes.com/en/festival/films/the-square。
[11] 同(10)。
[12] Director’s Notes,出处同(10)。
[13] 同(10)。
[14] 元首的秘书:《自由广场:关于人类困境的影像实验》[EB/OL] (2017.06.11)[2017.06.12]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595264/[15]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Feature Films Jury. [EB/OL] (2017.05.29)[2017.06.12] http://www.festival-cannes.com/en/festival/actualites/audios/press-conference-of-the-feature-films-jury-1
10 ) 政治正确、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艺术?
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先谈电影在欧洲现实语境下出现、获奖的意义,如何直面并反应欧洲社会中“政治正确”的问题,结合了电影中的几个案例;第二部分就电影本身的叙述和几个母题,具体讨论电影的“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再作分析。
欧洲戛纳获奖:呈现政治正确的两面往大了说,有着深刻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或欧美)也有着赎罪的传统;宗教精神潜移默化决定了一种世俗习惯,即审思、反省历史或当下的罪过或不足。
因此,为清除近代历史上由欧洲主导的各种殖民、侵略活动,二战后的欧洲,历经反思与赎罪,成为了最包容、多元、接纳的文明与政治主体。
这表现为后殖民主义思潮的风行,既强烈影响着文化界,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选择,使得欧洲从侵略者与殖民者,转变为了小心谨慎、担心冒犯他人的政治正确的坚决维护者;还表现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东)的动乱中,欧洲人非常用于承担责任,把如今的战祸、难民的流离归结为自己创造的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或是自己曾经的殖民史遗留的结果;在赎罪过程中,曾经在纳粹统治下极度排他主义的德国,更是走在赎罪与自省的前线,敞开家门,拥抱难民,世界人民一家亲。
实际上,从心理结构来说,自省与赎罪也给欧洲人带来了极强的优越感——正如拼军事实力的时候,我能侵略战胜你,武力上压制你;如今和平年代,比拼道德感,我能主动赎罪,能容忍包容你,也是因为我思想境界更高。
尽管外在的比拼形式变了(从军事比拼到道德比拼),但是欧洲人心理结构上的优越感仍然没有变。
但是话说回来,欧洲有着十足的理由优越。
军事是硬实力不谈,道德上一个懂得自省的民族,决然是比一个自以为价值观伟大的民族要优秀的。
欧洲沉浸于这样的优越感中,也是因为值得。
但要知道,心里上的优越没问题,赎罪与自省也值得推崇,但是有时自省过了头,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会带来新的问题,而不单单是纠正曾经的错误。
如今的欧洲,因为泛滥的政治正确而导致的逆向歧视(即主流的人活该被侵犯,而边缘的人做什么事都合理),已经成为了普遍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震荡中,大批欧洲人成了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上优越,过分地宽容,拒绝批判他者,生怕变回侵犯他人的“殖民主义者";不仅如此,这些政治正确的原教旨主义者却反向对自己人苛责严厉,严防死守,不准自己人发出批判的声音,直指批评弱者就是法西斯主义,而自己一定要成为卫道士,保护表面的和谐——因而,所谓的”弱者“就成了强权而肆无忌惮的”施暴者“,因为反正也不会受到舆论的限制。
我想,《方形》在戛纳获奖,仍然是欧洲优越感的一以贯之的体现,因为一方面,电影是一部反省、批判当下罪过的作品——要知道,这种自我批评、批判现实的作品,在某国可一定被看作是指桑骂槐的反动文艺,定要掐死于巧襁褓中——而欧洲人(主要是中上层阶级,代表人物是电影的男主角,即美术馆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当然也包括戛纳的评委和观影群体)乐于看自己被讽刺、被揭露, 不仅不藏着掖着,还给颁个大奖,这是自信的体现,也是优越的张扬。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这部鞭辟入里、省思当今的电影,绝不是愚蠢的“政治正确”的代言人,单单呈现某一方面的价值观,从历史的一个极端震荡到另一个极端。
正相反,电影尤为可贵地呈现了多声,这里有对人情冷漠的无情批驳,对弱者的关心——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也亦或隐喻、亦或真实描绘了弱者的人性之恶,以及政治正确泛滥情境下的荒诞现实。
导演虽然似乎意在讽刺中上阶级的代表,即美术馆的高级策展人,但在大多问题上,导演并不呈现明确的批判或是讽刺立场,而是选择代表性的现实拍摄为影片的素材,从而让观众自己选择立场。
因此,也许我觉得荒诞可笑的,其他观众可能觉得是正常无比的。
我举几个例子,来体现作者对“政治正确”两面性的反思,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欧洲(瑞典)现实的、不下判断地直接呈现:一、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去7.11取包裹,遇到坐在角落的女流浪汉,后者问他要钱,他笑着说没有,但是可以给她买吃的;她不耐烦,但也点了菜,颐指气使,指挥克里斯蒂安买个鸡肉三明治;克里斯蒂安转身去买,她继续吆三喝四,说三明治里不要洋葱,很是理所当然。
克里斯蒂安自己有事,但是还是给她买了,最后甩给她,留下一句:“你的面包,洋葱自己挑”。
在此,导演并未呈现任何立场;立场自然由观众来决定:有的人可能觉得克里斯蒂安虚伪,做假好人;有的人看来,觉得大快人心。
在此,我们不由反思:政治正确是否意味着弱者有理?
帮助弱者应该到达什么限度?
In your face二、在一场美术馆的演讲中,一个秽语症患者加入,在演讲过程中,屡屡大吼脏字,多次冒犯公共秩序,由弱者变为了施暴者。
与会者都是中上阶级的、有艺术品位的听众,文明教化甚高,但最后也几不可忍。
只见此时,一教化更深的大叔跳出来,让大家宽容这个骂脏话的傻帽,说他“精神受折磨,很难过”,让其他人忍受——于是其他人就继续忍受。
电影导演善用讽刺,不知是否在讽刺这个劝诫别人的大哥?
答案同样是两分的:有观众可能认同这个大哥,有的观众不认同。
但是,在场的人显然都是明白人,把这个满口秽语的人当做十足的傻帽,就像后来那个美国女记者就当着高级策展人的面,模仿、嘲笑这个秽语傻子的脏话;但是在演讲过程中,大家表面上都不说,都不去解决,不好意思把这个扰乱秩序者踢出门去,好似有极高的政治正确的门槛,无论如何都跨不过去。
闷声大发财三、电影行将结束的那个发布会,因为宣传视频犯了伦理的禁忌,招致了社会的众怒。
记者的提问十分好笑,也很讽刺。
一边是有人大骂高级策展人,利用乞丐做广告,而底层的人无处发声;另一边是,有人大骂高级策展人因言获罪、引咎辞职让言论自由无处容身。
这种两重性,是自由社会面临的长久问题,是政治正确和言论自由长期打架的现实。
——最后,在说到展览时,美术馆市场部的人意外跳出来,告诉记者展览的媒体稿件和图片都有,也顺便把展览的广告都做了…………报纸也照样报道了。
四、行为艺术那场戏,一个人扮演的猩猩大闹高端酒会,意义重大。
首先,这场戏很跳,感觉和叙事毫无关系——尽管这个猩猩人是电影中屡次出现的一个影像作品的主角,但是这些铺垫好像都是为了这场戏,包括其他地方“猩猩”或者“兽性”的在场或隐喻,都像铺垫的作用;而这场戏本身,又并不贴合主人公的人生脉络。
我不得不揣测,导演一开始就想要拍这么一幕戏,后来才调整剧情把这个片段融入到剧中。
基于这样的揣测,我难以克制把这场戏当做一个十足而完整的隐喻来看,和当今的局势联系在一起。
直话直说便是:这个闯入高端酒会中的猩猩,就是闯入欧洲社会的穆斯林难民。
行为艺术的设置是“丛林”,好似霍布斯论述的“自然状态”,即在没有外界强力的约束下,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彼此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不断的战争,残忍而血腥。
在这个行为艺术的“丛林”中,有一个野兽闯入,“人类如果软弱,就会激发它狩猎的本能”,这更加印证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斗争状态。
而人类如果逃跑,会被野兽猎杀。
由此,唯一的出路便是:屏息凝神不说话。
而结果呢?
就是屏息凝神的人可能不会被注意到,可以隐匿在人群中,安宁地知道:死的人可能不是我,而是别人。
果然,野兽闯入后,大家都不动,不说话,接受野兽的戏弄,有的人被惹怒了,试图叫停这个项目,根本没用,只得离席;最终,野兽跳到桌上,公然调戏一个女性宾客,她喊救命,没人理会;后来被揪着头发拖到地上,几乎要被强奸,才终于有一位长者看不下去,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单枪匹马冲了上来,继而,一直不说话的男人们才一并涌来,怒揍猩猩。
被猥亵的女人,仓皇逃命。
Attempted rape我们不难将这一幕联系到欧洲近来的状况,即难民来欧洲后带来的各种性骚扰和强奸事件。
反思这个行为作品的设置,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面对野兽,人类只有三个选择?
即软弱、逃脱或者屏气凝神?
为何不能一开始就猎杀野兽?
因为我们知道,这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
但是,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绝对不能没有边界,任由弱者满足本性,为所欲为,否则,后果便如上图所示。
宴会上的人,基本上是美术馆的赞助人,赤裸裸的上层阶级,因而,比之前提到的讲座的听众还要更加文明,还要更加能忍耐。
他们以为,只要文明地忍耐,一切都会好;怎能想到,上次讲座的疯子不过是言语上的,这次宴会上的野兽,带来了各种肉体上的伤害。
这场猥亵最终遭到制止,解决手段也没什么新意——文明人终于走下圣殿,仍然诉诸暴力,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欧洲人没有答案,他们深知政治正确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条路已经走得太远,甚至到了不能接受批评政治正确声音的地步。
但是,《方形》至少呈现了“政治正确下”好心时而带来恶果的悲苦而矛盾的现实。
这部电影虽然批判政治正确,但是至少(通过直接表达和间接隐喻)呈现了政治正确原教旨主义的荒诞。
能呈现这样的现实已经不容易。
这样的呈现让人想到了德国艺术家Christoph Schlingensief的2000年的一个艺术项目,以电视转播的形式出现,名为《Foreigners out! 》。
他邀请了在奥地利的多位移民(据说为真移民,实际上并没有人知道真假)来到一个城市中央,住在一个箱子里,通过电视直播他们的生活,然后由奥地利居民每隔一段时间投票,选择一个人,不仅驱逐到箱子之外,也驱逐出境。
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广泛参与,也出现了针对难民的各种声音。
Christoph Schlingensief只是将项目进行下去,并未支持任何一方的声音,而是呈现民众的多声。
由此,我们看到左翼和右翼的争论,看到结尾左翼如何拆墙打洞、以暴力的形式,推翻了这个节目,“解救”了这些难民——然而只有Schlingensief自己知道,这些难民是真是假。
我有如此短评:Schlingersief’s film project about refugee was made to objectively re-enact and reveal the reality, and let the citizens drawn into the project behave and make the choices totally on their own. The result is a “happy” ending—with the pro-refugee citizens won the campaign, but as audience, we see how these peace-advocates won the campaign in a violent way, as if self-claimedly holding the morally correct proposition, they could then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win, to fight violently for humanity. 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艺术?
如果把导演对政治正确两面性的客观呈现当做他对社会的冷眼旁观,那恐怕错了。
多次将镜头对准婴儿与流浪者,就是他左翼关怀的明证——尽管,恐怕他自己也纠结于到底多少左翼在做促进平等的事,而又有多少左翼只是利用平等的话语而渔利。
所以,他一边批判讽刺,一边感同身受。
这些矛盾情绪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主角,X-Royal美术馆的高级策展人,克里斯蒂安。
他身上有社会的荒诞,有群体与个人的冷漠,更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的踪影。
如果导演是不加夸张地描绘瑞典,那么北欧的天堂也充满了不幸:不止一次的,呼救的人,没人理会;乞丐行乞,无人搭理;介绍菜品的厨子,没人在乎。
这个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尽管在外人看来有优良的福利制度和活跃的公民社会,但想不到社会原子化仍然如此严重,人人各自为阵,事不关己。
电影的音乐和画外音很有控制,并回环往复。
主奏是古典乐与人声的结合,辅佐它的是多次出现的“救命”、婴儿哭、狗叫的社会声音,这也是主人公心中用来不断拷问自己的问题与怪象。
主人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手机和钱包被盗了,但是他是在完全不想被卷入救人情景的状况下,恰巧做了“英雄”,还成为了悲剧的英雄,被别人陷害了。
这个时代,连穷人都不容易,因为安静地乞讨、或是小声喊救命,是无人理会的。
只得装疯卖傻大喊救命,制造动乱,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
电影一开头,在爆裂的兽性和冷漠的人性相互更替的时候,很快沉入了往日的安宁,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
整个图景,都是荒诞的。
于是,回到艺术的问题。
艺术在这样的社会中,做了什么?
能做什么?
电影的同名艺术作品是《方块》:方块是信任和关心的圣所,在它之内,我们同享权利,共担责任。
是吗?
艺术界恰恰是最尴尬的地方,是信任和关心的圣所,也是怀疑和伪善的家乡。
乞丐们苦苦祈求1克朗,并没有人理会;镜头一转,X-Royal美术馆却获得了5000万克朗的赞助。
艺术圈讨论着艺术和非艺术的问题,空间和非空间的问题,试图拉平生活和艺术,追求着社会的平等,却是自说自话,无人理会,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的美国女记者都整得神经质了。
最明显的讽刺是克里斯蒂安给小孩录视频道歉的那一段:他起初在道歉,反思自己的不对;进而联想到自己的不对是因为对小孩所住的贫民街区的恐惧;进而讲到社会阶级的区别和区隔,并开始掉书袋地细究原因,认为这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原因,好似在为自己开脱。
艺术界真的很可悲,但是克里斯蒂安是否真的那么可恨?
尽管电影语言似乎都导向于对他的讽刺,但是他何尝不是这个世界(包括艺术世界)中一个真实的男人?
他所代表的,正是荒诞与冷漠下的真实。
他自私而自我保护的欲望极强,两个较大的道德疑点是:一夜情后还生怕女记者控告他强奸,始终手握着安全套不放,之后也不承认他们的一夜情;他为了找手机有些不择手段(在别人的建议下),惹到了小孩,也不第一时间道歉。
就男女关系而言,他承认权力给他带来的好处,并以此为乐——尽管,在多大程度上是欺侮了女记者倒是难说,因为不知是否他们你情我愿;就给小孩道歉而言,他拖延认错很久,但是却一直受良心的谴责,并终究回归了良心——不顾形象翻垃圾堆,并登门道歉,尽管为时已晚。
但是,也许正如他说的,他的自私、自保,也有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原因,这既是他的说辞,也是真相。
他表面上倡导平等、关爱这些《方形》所代表的良善,自己所作所为却差强人意——然而,他终究受到良心的考验,他也终究在自己的展览中推广良善。
往差了说,他是知行不合一的伪君子;往好了说,他是在维持现实最基本需求(自私、自保)的基础上,仍然在艺术领域中努力做着些什么,以推广《方形》的理念。
回头看来,他是好领导,好父亲,他似乎没有电影讽刺得那么邪恶,只是没有成为道德与行动上的完人。
这是他个人作为策展人的困境,也是有良心的当代艺术在社会中的道德困境。
如果将这部电影理解为对克里斯蒂安的无情嘲讽,那么我们又是在占据道德高位而瞧不起别人了——除非我们也能自信我们能成为道德与行动上的完人。
我们要感同身受,要同情之理解,更重要的是要清醒而不自大。
艺术,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电影艺术,已经是那么无力了。
那么至少,也要清楚地面对自己的位置,面对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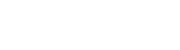



















































在两个人类释放性欲(动物本能)一旁,真猩猩抹抹口红、翻翻画册(人类文明);在一群人类共赴晚宴(人类文明)面前,假猩猩赤膊上阵、动手动脚(动物本能)。
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的种种无力感,虽然没有难民出镜却给出了欧洲难民问题最好的隐喻,各种戏虐桥段飞上天,文明如何去对抗无知和暴力,无中生有的求救声,就像哈内克躲藏中的隐藏摄像机,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只能寄期望到下一代了。
总而言之,不如《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太聒噪,中产阶级散发的油腻白左气质与直白到近乎虚伪的讽刺实在让人难以看下去。要想在影像中触摸到当代艺术、博物馆学与艺术品展览机制完全可以去看蔡明亮的电影。
勉强及格。其实线索挺乱的:男主在街上想助人为乐一把结果被套路走了手机钱包,他通过定位手机威胁整栋楼住户(他自己也承认对该街区有偏见),由此陷入一男童的讨说法并开启自保模式。另一方面,男主作为艺术策展人启动了一项概念领域“方块”,这是个呼吁人人互助的空间,看上去像这些维京人后代展示现代文化语境下自我阉割效果的汇报,然而这一切很快被戳爆,宣推方用了一个类似伊斯兰国的自爆广告推广之,引发舆论反弹。这片里还塞入了一夜情女记者、模仿猿人表演和秽语症病人等角色,不断的突破冒犯公众或男主的个人空间。这片子的主题与其说是讽刺什么,我觉得是人类所谓现代性内部的天然矛盾(私有制、公共交际规范、消弭不平等)。导演的手法聪明,很多镜头很精致,晦暗走廊里塞信那场戏看得我也很紧张,不过并不雄辩反倒透露出些迷茫
立意于对艺术遭遇尴尬的嘲讽、对中产阶级的自嘲,可片子内容本身到处是这种尴尬和装腔作势的气息。
一个trap,最后人猿模样冲入晚宴的Oleg依然懂得遮羞
IFC center at Manhattan; 老美的笑点真奇怪 从头到尾有人笑;啪啪啪那场戏太好玩了,海报一幕简直惊呆;觉得有一些寒枝雀静的影子;这几天也是巧啊,先是看了《挚爱梵高》,接着就在MoMA欣赏到了梵高真迹,然后接着就看了这部关于博物馆的电影。
规矩事不规矩,文化人没文化。2.5
有些部分还不错,但仍然是他们那一套,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会改什么也不会变甚至不愿意改,既得利益者也不会放弃他们到手的好处,于是成了一个个观点只有观点没有行动。虚伪和伪善。要不是喜欢的女演员根本不会看,然而她还是个扁平不重要角色,甚至还追寻爱情,再次印证一些白男导演的虚伪
没办法给高分,主角像是游走在线条之外的人。剧情之内的讽刺,大家心知肚明但不一样为了灯光与红毯,义无反顾吗?艺术感是强,艺术+现实。要么是黑色空间的一抹白点,要么是红绿不分的一锅乱粥。什么是真实的,方形内外都是真实的,我们探索的根本,大概是线条,而不是形状。
单独段落拎出来看有不少很亮眼的,但总体这么拼起来就感觉散的一地都是,没有一处真刺下去的 7.2分★★★☆
7.5/10。尴尬与自嘲,好几幕都忍俊不禁。野兽表演,炮友逼问,发火的男孩,可回味的点很多。但形式感过重,骨子里透着一股自恋感。
界限的故事。阶级之间是不是真的终归很难互相理解呢?艺术又可以自由到什么边界呢,,,,无解的未来
totally weird me out !
这些年来头一次不知道放映厅里观众笑的是什么,不止一次,感觉是影厅里的笑声而不是荧幕上的故事让人更不安。当今语境下,消费“自嘲”总归比消费艺术本身更政治正确吧。立场含糊,说是自嘲少了点坦诚,说是黑色荒诞又不像个完整的寓言,片段间需要补白的地方太多。故事精巧,甚至精美,但自圆其说吗?
表面上是自黑,骨子里是对廉价反思能力的自恋。导演这种自以为是和宴会上蛮人如出一辙,不存在真正道德“困境”,不存在和观众探讨和交流,而只剩洋洋得意至上而下的展开对观众无根基的羞辱。但这种羞辱本身又纯靠意淫。
超现实主义的荒诞喜剧,颇为精巧独特的设定。然而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嘲讽,到头来还是因为自身价值观的摇摆而显得犹豫而浅尝辄止,不知不觉陷入了与被嘲讽对象的相同的困境。
完全跟《游客》的内心刻画没法比…又长又聒噪。
像一场不怎么闹的闹剧,讽刺点很多但并没有一条特别深入或者值得剖析的,节奏相比悲情三角也是慢很多,还是喜欢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