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魇疯人院》剧情介绍
备受梦魇折磨的年轻男子让·伯洛特(帕沃·里斯卡 Pavel Liska饰)反复做着同样一个梦境:两个恶魔闯进他的卧室,把他推进了疯人院。心力憔悴的伯洛特偶遇神秘侯爵马奎斯(杨·特里斯加 Jan Triska饰)。这个扬言要救治伯洛特的怪异侯爵,引诱伯洛特来到一间阴森恐怖的疯人院。黏着的空气,病态的疯人,黑暗之中穿插的“生肉表演”以及一系列令人作呕的放荡作为,让失魂落魄的伯洛特彻底崩溃了。当他从看似纯美的护士夏洛特(安娜·吉赛罗娃 Anna Geislerová饰)口中得知院长和侯爵的丑恶的面目时,这场炼狱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部由捷克电影和动画大师杨·史云梅耶创作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梦魇疯人院》,荣获2005年皮尔森电影节最佳影片,2006年捷克金狮奖最佳艺术指导、海报设计等奖项,并代表捷克参加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史云梅耶在开篇就警告世...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绿能战士危情杜鹃第十王朝宝贝快跑精灵宝可梦:幻影的霸者索罗亚克大师们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第二季休赛期败犬:后篇超级英雄51区人蛇大战金枝玉叶假面骑士×假面骑士Wizard&FourzeMOVIE大战Ultimatum鬼娃恰吉第二季遭遇陌生人浴火危城哈桑的义务海之谣一个女孩的舞蹈疯狂之家弃子西风烈斯图神父爱笑种梦室之东北佳人艾娃非缘勿扰机甲拳击第二季三次为定蜘蛛侠:英雄远征
《梦魇疯人院》长篇影评
1 ) 重新发电
人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
——齐美尔杨 • 史云梅耶的电影《疯狂疗养院》,同时从爱伦 • 坡和萨德侯爵那里获得灵感,讲述绝对自由,以及文明的操控和压制。
片头导演现身说法,竟然首先强调这部电影与艺术无关,所谓艺术早已被夸张的渲染所代替,电影不具备丝毫的艺术性,只是关于如何建造疗养院这个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大体存在两种方式,两种都是极端主义,极端自由的和极端保守的,皆筑基于监禁和惩罚这个共同的基础,当然,也许还有第三种,就是集此两种极端主义于一身。
我们希望从城市展的角度探讨艺术展,城市演变为大都会,正是集此两种极端主义于一身之表现,大都会早已将自己从城市那里继承的政治遗产,统一安排在自己的分割符之中。
艺术也不能幸免,虽朝暮弹唱,虽放任自由,也终不过是被监禁于大都会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边沁监狱之中,膜拜在招摇过市的“札格纳特”,这个马力巨大又失控的景观装置面前。
只有在此意义上,重新发电,才成为一个问题,发电厂早已搬离,巨大的躯体转化为失控的城市遗产,失去了原本的使用功能,被抛入来日方长的世界。
发电厂的未来不可预知,可能是古董,可能是垃圾,也可能是艺术作品,全在于如何重新发电,如何做到真正的重新,重新发电,不是为景观装置输送新能源,进行一种好大喜功的嘉年华式阐发,发表欢迎拍砖的宣言书将砖头积累为自身绚丽的颁奖台,重新发电,不是为景观装置挂上复活节的游行彩车,装点招摇过市的行进路线,以影像和文字游戏传播自身肤浅的诗意和懵懂的青春,重新发电,也不是为景观装置提供向未知领域进发的可能性,将对生存方式的资源性命题转化为无差别的牟利行径,自封某某人士将他者视作未被开发的矿藏一般颐指气使自以为是,还揶揄还支招还法外施恩还昂首天外。
重新发电,就是绘制地形图,行动中的再生产,营造出一处心灵脉动的共同体场域,在二维的投影上重新理清三维运动的深度和广度,并借以新视角返观二维世界,“札格纳特”的铺陈改变不了景观装置表面上的匀质性,三维运动的波澜起伏也远远超乎二维观者的想象。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层级复合的空间之中,二维投影的世界拥挤却留给三维运动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城市展还是艺术展,都是捕捉此三维运动的专门技术,而非在二维平面上的简单搬运。
重新发电,就是跳出二维空间,重新发现投影之外的世界真实,就如同重新发现景观装置背后的来日方长一般。
景观装置终结了城市的历史,但其自身也旋即被历史的城市所终结,城市展或者艺术展,作为此终结之再终结,正如幽灵一般死死萦绕在景观装置的周边,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重新发电,就是无条件投入这样一场持久的战斗之中,在战斗之中,积累继续战斗所需的弹药,勾勒未来都市行进的路线,保全社会群体再生的能源。
2 ) 这世界是个巨大的精神病院
而这个表面上是精神病院的世界,背地里还是被有钱有权者掌握着的女支院。
最近美国那边爆出了爱泼斯坦事件,让我不得不回想到这部电影里的种种和《大开眼戒》里的情景,虽然这部电影的原著我没看过,但是根据导演拍出来的最终的样子,总让我觉得我他们有共通之处,其实讲了一样的类似的主题和寓言般的故事。
无论掌权者如何更迭换代,其实都是同一类人,无论你站在哪一方,最后同样都是兔死狗烹的结局,还有出路和解决方法吗?
3 ) 直呼過癮的瘋狂
仍在世的大師之中,楊·史雲梅耶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儘管他的電影都有統一的風格,但你每次看都會被他天馬行空的思想所吸引,今天忍不住,看了他的《Sílení》,楊在開頭說這片與藝術無關,僅僅向愛倫·坡和薩德侯爵致敬,這不如得讓人想起另一部改編薩德侯爵著作的電影《薩多瑪120》,這部電影肯定也有讓人難以忍受的畫面,的確,電影本身充斥著很多活動的“物體”,例如被割的舌頭,腦子,眼珠,一塊塊的肉,不過鄙人覺得一點也不惡心,反倒有一種難以言明的詼諧在內,這在楊其他的電影都有體現,電影劇情也很有意思,兩個極端主義的對抗,尼科爾森演技沒得說,既然導演都說與藝術無關,有興趣自己看吧
4 ) 这个世界把我逼成精神病,那我就把这个世界变成精神病院!
看看现在的人,随随便便都能被冠以各种病:被害妄想症,中二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等等等等。
为什么有这些病的存在?
只因为某些小群体状态或者形式比较与众不同,然后大部分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正常,就把与自身相异的就称为'病态','畸形','残疾',如此大家都有病,这病就叫'正常病'。
人生来独一无二异于他人,因此人人都有病。
而人的组成无非就是肉体和意识,要达到肉体的一致很简单,死是最快的捷径,要达到思想的一致很难,因为思想从不随着肉体的毁灭而消逝。
这个世界本是精神病院,我们都是精神病人,我们最大的疾病便是我们对于人生而自由这种思想的忘却。
所以,能救赎我们的,从来不是上帝,而是自由,并且只有自由。
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人生的枷锁似乎伴着我们出生,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沉重。
我们不堪重负,于是寄希望于有人与我们一同承担这沉重的枷锁——限制自己的同时苛刻地去限制他人,这是互相的——统治者们用钱,用名,用利,用权,用武力半引诱半强迫地给你套上本应是他们的枷锁——佩戴枷锁的人越来越多——枷锁只会变多变沉而不会变少变轻。
终有一天有人承受不住,终有一天有人于心不忍,终于有一天有人记起了自由——他们想要摘去自己和别人的枷锁,即便不能摘去,也抱着最小的希望:稍微减轻枷锁的重量。
但自由不是教了人人就都能学得会的。
于是,那部分觉醒的想要挽救自己的同时挽救他人的人,选择了两条路:1.推翻单方给予枷锁的统治者。
2.开化更多渴望自由的人不再互相给予枷锁。
乍一看来,第二点似乎是第一点的基础,因为貌似只有更多渴望自由的人出现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专制统治者。
实则不然,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必去知道自由是什么,只需尝到自由带来的枷锁重量的减轻的甜头,便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可最难的是,怎样让他们尝到自由带来的枷锁重量的减轻的甜头。
因为长久的“病患”,他们丧失了味觉,别的知觉也趋于麻木:舌头适应了苦味,肩膀也习惯了沉重:给他们甜食,很多人起初是适应不了的,而摘下他们的枷锁,他们环顾四周反而心生疑虑——别人都有枷锁,我怎么没有?!
本来就因为异于他人而被冠以有病的名头,现在和有枷锁的大众差距更大了,那病是不是更重了?!
不过还好,在他们的知觉慢慢恢复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会为脱去枷锁而欣喜了。
已经觉醒的那部分人在开化未觉醒的那部分人的道路上走得很艰辛。
他们尝试着各种方法,起初都是循循善诱的劝导,但是不难看出这个手段的效率并不高,从而演变出了半冷不热的嘲弄和看似荒诞不经的讽刺——这个手段效率高了风险也高了——要知道,有些人是宁愿不要自由也要去维护自己那一丁点仅存的自尊的,结果他们像个反叛期的少年少女一般,半句中肯的话也听不进去,甚至于完完全全地抗议对方的每一句话!
不过还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的人占大多数。
殊不知持半信半疑态度的人是最难去争取的那部分人。
专制统治者们占了太多优势——钱权名利,可已经觉醒的那部分人能给予的只是一个希望,被唤醒者能想象,却看不见,也摸不着。
即便有人对钱权名利没有企图,也可能会被棍棒给打败了,或被别的东西给诱惑,就像这部电影里的男主角对那个荡妇的被利用的爱情。
如此的种种使得专制统治者们很容易在这场角逐中获得胜利。
最后的结果,可能就像电影里一样,专制统治者们又成为这个精神病院里的医生,囚禁所有人,依靠对肉体的鞭笞来磨灭人的意志,寄希望于民主改革,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经的侯爵却被关押,被可耻地用毁灭肉体的方法来压制思想,而这结果的造成仅是因为他试图去帮助那位“时常做噩梦的,半信半疑的”男主角。
民众的判断决定了他们生活在一个看似怪诞但是自由的精神病院,或者是一个依靠枷锁和肉体上的鞭笞因而看上去秩序井然的精神病院。
——————————没啥特别的分割线————————————杨·史云梅耶的隐喻太强大了,个人浅薄地说几点自己的看法。
1.我作为一个轻度生肉恐惧症患者彻底拜倒在他的那些看似可怖的生肉的石榴裙下:有些人是条舌头,耽于口欲;有些人只是眼睛,只会看;有些人只有脑,但不能表达,而大多数人只是块会行动的肉,不会看,不会尝试就更别提思考了。
2.伯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以及怪异的举止看似很无端很邪恶,跟后来出场的医生相比就更加,其实是对众生被困而不能醒悟的嘲笑以及为了唤醒男主角而做的比较极端的举动,表达了导演恨人们分不清看似正义的荒诞和看似荒诞的正义,只会感性地去看一个人的表面却不能探究其深层次的意图。
(经朋友提醒,向侯爵表达最高的敬意,也向校内上的)3.男主角的梦魇也是你我的梦魇,害怕被囚禁害怕失去自由。
4.女主角的存在则是为了表达:邪恶的东西外表总是那么有迷惑性,对其应该〇容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在精神病院看到的精神人看似怪诞,却是这个社会的完全写照。
往人身上泼墨的和甘愿自己当画布的——艺术家;拿刀刺坏枕头的——暴徒;拿了刀自己私藏的——小偷;喂鸡的——农民等等等等,每个人都不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子。
表达了这个世界就是精神病院,或者说,精神病院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
6.导演为什么强调说这部片子是恐怖片,恐怕不是单纯的因为这片会给生肉恐惧症和家禽恐惧症者带来不适吧?
是因为杨·史云梅耶对这个世道的了解清醒到近乎残酷,他就是要赤裸裸的把这恐怖的现实摆在你我面前,不会因为我们的拒绝和不承认而改变。
因为迟钝,很多想的描述不出来,暂且先写这么多。
5 ) 疯子一箩筐
依然是史云梅耶的招牌风格,乱跑的五花生肉,各种人体器官的特写和运动,特别是黏糊糊的舌头和转动的眼球。
疯癫的角色,不论医生、护士、院长还是病人,都在这个压抑、病态的环境里完美融合。
这种癫狂加恶心加预言式的故事在关于精神病院的电影里几乎是标配,病患永远有真疯的和理智的;护士在长期的工作中习惯甚至享受治疗病人以及与掌权者交欢的乐趣中放弃自我审视和道德感,变成一个机械的行刑者;医生作为权力者进行着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人体实验,道德更是彻底沦陷,但作为治疗又将其合理化甚至道德化。
影片里木讷的男主每次被两个光头男人架出房间时总让我想到了《致命ID》.......影片后半段的疯人院大革命将被治疗对象调换了一个阶级,随之而来的是治疗方案由自由艺术派转变为强硬的身体惩罚以此平衡思想的疯癫。
而进行惩罚手术的医生则对此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这种典型的医学狂人经典形象充满了隐喻。
挖眼手术的过程用被包裹的五花肉代替,每个人都是疯子,抑或每个人都被指定为疯子,成为权力机器下无能为力的棋子。
这样的电影总会让人想到福柯,想到疯癫与文明,想到理性的非理性色彩和理性达到巅峰时便进入到疯癫的论述。
这样的故事始终逃不出这些元素,也很难解读出更多东西。
而史云梅耶加入的定格动画部分倒是给观众带来了动画与真人对号入座的新鲜感。
6 ) 血肉狂欢
曾经一度沉迷于各种怪诞电影。
衷情两个小时的影象刺激。
这些电影的导演本人很少去记住他们的名字和来头。
只知道,诸多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更是乐于冲击传统美学的自我主义战士。
漫漫长夜,抑郁侵袭时候,此类片子是最好的麻醉药。
得以窥视他人脑海中天马行空的想象是快乐的。
最少,能哄好我的怪异神经。
喜欢爱伦坡的人会爱看,因为整个剧情简直就是坡小说的大合集:《红死魔的面具》、《乌鸦》(片中是白鸡)、而侯爵母亲被埋那段的灵感是取自《鄂榭府崩塌记》。
除去视觉系动画、时空错乱,故事情节同样怪诞不经。
真的不是艺术电影,它渎神、逆经叛道、无休止地展示恶心。
但也不仅仅是视觉刺激,是在黑色幽默的名义下对自我辩解的嘲讽、对是非曲直的怀疑。
通过讲一个疯狂的故事来思考极端的辨证关系: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
照我的看法,片子虽然到处充斥着新鲜的肉块和器官,但是每次它们的出场都带着拟人的动作和激昂的革命音乐。
不论是生肉(大概是猪肉)舞蹈、内脏暴动、眼球爬进头骨、舌头交合,用动画的表现手法还有那么一丝丝可爱的意思。
最少是冷幽默的。
当然,如果是有洁僻或者从来没下过厨房的人,应该相当受不了这种肉肉的真实。
影片一开头的猪下水足以把你唬一跟头。
片子中的羽毛人、从雕像的眼口乳房中窜出的舌头、模仿法国大革命的疯子聚会、侯爵对上帝的漫骂,昂然响起的马赛曲,是经典。
随便说句,男主人公的眼神让我想起约翰尼德普。
也许,拍这种神经叨叨的片子必须纤细脆弱、满脸无辜。
作为一部有阴暗情节的影片来说,根本不算压抑,也没有让人透不过气的局促感。
节奏也够流畅,我想这都得益于大约十分钟就出现一次的血肉盛宴。
再强调一次,那些肉肉真的很幽默。
7 ) 好片子~
什么是好片子,能看懂就应该是好片子吗?
对“看懂”的含义指的是剧情吗?
能看懂剧情难道就能真正理解导演的意图吗?
一部片子如果看“不懂”是否就该否定它的价值?
单从剧情上看,此片我也并非能看懂,但我决不否定它是一部好片,就好比音乐,虽猜不透歌里的词,但仍会被曲调所感染,杨的片子就有如此强大的气场,疯狂的吸引着我,他的每一帧镜头,每一处残败的场景,每一枚摆件,每一次吱嘎的声响,每一出疯狂的特效,都弥漫着难以琢磨的魅力,无不让我着迷,赞叹!
他的电影属于有触觉和嗅觉的电影,这种感受能和我的内心发生摩擦,产生一种粗粝的,难以割舍的情感,这正是电影感动我的地方,我认为多数时候,它表现的是最真切的现实,一种可以让你看得见,摸得到,闻的着的现实,只不过被一个疯狂的,具有细微的敏锐观察力的人用自己独有的一套手法夸大糅合了而已,它是一个利用超现实手法表达自己想法的,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
8 ) 一块猪排的一生
文_发不沾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在进入新千年后,杨·史云梅耶的创作步伐逐渐放缓,他开始将自己的创意浓缩进一部又一部长片之中。
作为捷克当世最“牛叉”的超现实主义大师,老杨将他对人和物的驾驭能力,更为纯熟地展现在了[梦魇疯人院]之中。
尽管有人认为,影片并未体现出史云梅耶逆天的想象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犀利和深刻,一如既往。
当我们在距离影片上映10年之后的今天,再度踏入电影里的疯人院,会发现,那些关于挣扎和反叛的旧事,仍和电影里的生猪排一样,鲜嫩多汁。
食色性也饮食与男女,不仅是史云梅耶向来乐意编织的衣裤,同时也是他所热衷使用的丝布。
在前两部作品[极乐同盟]和[贪吃树]里,老杨先后将性欲和食欲,包装成诡谲另类的炮弹,轰炸着观众的心理防线。
而到了[梦魇疯人院],老杨虽说在“作恶程度”上有所收敛,但那些扑面而来的Cult气息,仍令大部分人猝不及防:匍匐的大脑、蹦跳的眼球、交媾的猪舌以及口腔的特写,都令人带着怯怯的兴奋和莫名的不安。
和史云梅耶以往大多数的作品一样,食物在[梦魇疯人院]里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老杨说过:“食物是我常用的一个主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身的一个困扰。
”童年时期的史云梅耶,是一个厌食症患者,曾被送到疗养院强行喂食,这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却成了他后来的灵感源泉。
老杨认为,“人们对待食物和食用食物的方式可以很好地反映他们的文明”。
在[贪吃树]里,他用“吃”这一行为本身,揭示了无节制的怜悯所带来的恶果;而在[梦魇疯人院]里,“吃”成了侯爵“权力”的标尺,在他的那场“黑暗弥撒”里,巧克力慕斯和身着修女服的少女,都成为了他享用的“美食”。
至于与影片交互进行的,那些定格动画中翻山越岭的猪肉,更是早已成为史云梅耶电影里的“常客”,它们继承了老杨的短片[肉之恋]里嫩肉的身手,攀爬跳跃,生动活泼。
在电影开场,老杨本尊现身,为观众打下一剂“预防针”:“你们将欣赏到的是一部恐怖电影,它充斥着夸张的渲染,毫无艺术性可言……”接着,他又把创作背景和影片主题一一点明。
然而,当我们在欣赏完电影后,也许更多的感受会是“被老人家耍了”,而非“原来如此”。
电影的故事来源于爱伦·坡的《塔尔博士和费瑟尔教授的疗法》,这部短篇小说为影片提供了骨架,而当我们翻看老杨的创作履历,也会发现,混杂在他天马行空的创意之中的,是其对爱伦·坡的情有独钟,他曾先后将坡的小说《厄舍府的倒塌》和《深阱与钟摆》拍成短片。
除了爱伦·坡,另一位被史云梅耶点名致谢的,是“赫赫有名”的萨德侯爵。
萨德以《闺房哲学》和《索多玛120天》“闻名”于世,此人所背负的争议,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一直延续到今时今日,而以他名字命名的“萨德主义”,更是SM中的“S(Sadism)”的滥觞。
老杨在一次采访中坦言,自己并不认同萨德的道德观,但他也认为“没有反叛的生活犹如一潭死水”。
电影中的侯爵一角,即是萨德的化身。
他满口渎神的言论,放肆而充满诱惑,他是纵欲的先锋,也是堕落的魔头。
他用一段振奋人心的宣讲,动摇着主人公伯洛特的信仰,“肉欲和罪恶是我们的天性。
”困肉之斗这部电影的“打开方式”,其实很简单,一如史云梅耶开头所言,“这是一个主题鲜明的电影,故事的核心是如何经营一家疯人院”。
电影里,争相控制疯人院的势力有两股,其中一方,是以孔米埃医生(Dr.Coulmiere)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用禁闭、电击和惩罚来“治疗”病人。
控制是他的信条,因为“一个疯人院没有地方容纳自由”;而另一方,则是以马洛普医生(Dr.Murlloppe)为首的自由派,他为病人提供“预防性治疗”(一种为了防止病症突发时的束手无策,而进行提前模拟体验的疗法),并赋予他们完全的自由,“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如果病人认为自己是头驴,那么就喂他吃草。
而侯爵,无疑是自由派最大的拥趸,他反对一切精神和肉体上的禁锢,在夜晚举行黑暗的弥撒,用不敬的唾骂代替虔诚的祷告,把庄严的圣餐变成淫乱的聚会,然后在自由的领土里建立起强权。
主人公伯洛特,在马洛普医生掌权的时候,进入了疯人院,他看上去一脸无辜,略带神经质,这正和他“棋子”的身份相得益彰。
与伯洛特相对的,则是看似纯洁的护士夏洛特。
她和伯洛特,都在疯人院易主的风波中得以幸存,但不同的“功能”和性格决定了两人的不同境遇,像伯洛特这样的人(而且是男人),永远是第一批“中枪”身亡的,而夏洛特那样的人(况且是女人),永远排在队列的最后。
和大卫·林奇一样,史云梅耶的电影都如梦境一般复杂奇幻,只不过林奇的那些“噩梦”源自他长期坚持的超绝静坐,而史云梅耶则更多地诉诸于自己的童年,从记忆深处获取灵感和情绪。
但相似的是,他们的镜头最终都成了他们各自潜意识的“画笔”。
那些荒诞和癫狂,都是最真实情绪的体现。
老杨说过:“我不会限定人们对我作品的理解,因为我的电影不是论文式的,不会在开头提出一个概念,然后发展它,并在结尾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如果说他的电影是一个超级大卖场,那么观众就是顾客,从中各取所需,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要知道,从来没有只卖一种商品的大卖场。
对于[梦魇疯人院],老杨只做过一次阐释:“它主要是关于自由,因为有关自由的主题,是我仍坚持艺术创作的唯一理由。
”自由魔圈将电影定义为恐怖类型,许多人一定会不买账。
比如说电影开场不久,那头被开膛破肚的猪,与其说令人惊恐,毋宁说令人作呕。
此外,那些活起来的肉,在欢快的进行曲陪衬之下,只能用滑稽来形容,它们争先恐后地钻进时钟、涌入地窖,就像是伯洛特,面对夏洛特(美色)时的奋不顾身。
那些肉片最后不是被纱布裹成“木乃伊”,便是进入绞肉机,化作肉糜。
因而,定格动画的段落也可看做是对影片主体的注释,或者,按照史云梅耶的说法,是一种“渲染”。
[梦魇疯人院]的恐怖,与[异形]那种制造未知恐惧的恐怖片有所不同,也远不及各路灵异怪形来得吓人。
电影最令人感到后怕的,是自由的朦胧。
这种朦胧感,又因为老杨的再三揶揄,从而变成遥不可及的幻梦。
同是捷克人,史云梅耶与老乡米洛斯·福尔曼对待自由的态度,截然相反。
尽管两人都曾将一整座疯人院搬上银幕,但老杨的[梦魇疯人院]却从一开始就抹杀了飞跃它的可能性。
他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自由和未来的不信任和无期待。
比如,为了贯彻所谓的“艺术治疗法”,释放一些病人的“艺术欲望”,就需要另一部分的人充当“画板”,而这其中的“强制性”,自不待言。
又如,侯爵指使真人摆出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造型,而扮演其中“自由女神”的正是夏洛特,老杨用萨德的方式对这幅画进行了“再造”,让袒胸露乳的女神遭受人民的侵犯。
而倘使我们把夏洛特对伯洛特的“引导”与之对号入座,那么老杨对自由的悲观论调就显得愈发地清晰。
自由,到头来,竟和钳制殊途同归。
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的“无缝跳接”,虽是史云梅耶的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因为历史本身在之于这个问题上的“对策”,一向不具备丝毫的创意。
在老杨眼里,所有的文明,最终都将走向消亡,而在消亡来临前的一切,都不过是人类的自娱自乐。
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包含着无尽的轮回和不可逆的宿命,无论是早期的[石头的游戏]、[公寓],还是后期的[对话的维度]和[食物],都试图向观者灌输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
如是观之,[梦魇疯人院]不外乎又一出史云梅耶式寓言,就像他在[其他]里所展示的第三个故事里,那个永远在画房子的人。
自由的进程,在老杨眼中,正是那座无论怎么画都画不好的房子。
影片也在结尾回到了“兴亡盛衰一场空”的语调里,电影的开始也正是电影的结束,老杨习惯性地画了一个圆圈,对参与这场“游戏”的人来说,他回到了起点;而对一块猪排而言,它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于是,最后的镜头里,配乐一改先前的欢愉,变成了哀悼之乐。
人类的世界和猪肉的世界,也在这一刻,合二为一,那些生肉,被塑封起来,在超市的货架上叹息。
刊载于《看电影·午夜场》2015年二月号
9 ) 我后知后觉想到了很多 至少不是一个个的标签那样 但我尽量不说 当成秘密好了
电影一开始史云梅耶就讲了 感谢萨德侯爵;关于对疗养院(精神病院)病人的治疗的方式上,两个极端方法的探讨。
这个故事就已经算是讲完了。
(没想到的是精神病院也是萨德侯爵的归宿,那伯洛特不刚好是萨德的反面嘛 ,为什么也得把他弄进去 ?
喔~原来他们眼中伯洛特才是真正顽固不化真正该死之人呢)听了听萨德写过东西,回想伯洛特是怎么推动这件事发生的,“善与美德的努力是无望的终将遭到失败和毁灭”。
伯洛特有真实的怜悯,信任,恐惧,和对爱的渴望,正如我们跟着他的心里状态来判断好坏人一样,然后就听到有人对你说:不用担心,我会治愈你…好了,恶的有效性凸显了。
还想谈到一点就是,萨德侯爵的世俗不可容忍的性观念,在这部电影里倒反转成可以玩味的自由思想观。
也挺有意思的,这就好比一些恐怖片里前调再诡异再迷离拍拍脑袋梦醒了,就都说得通了,精神病院也是他的造梦所,这片自始至终都是病人们的世界好吧,哈哈哈哈哈(虽然我脸盲,但我有高矮胖瘦有没有胡子的分辨标准)
抑制精神我没法再被迫思考了因为我一天爬不了两次山 再成瘾者也避免不了身体的限制 身体受限 精神获救
天冷了 请喝茶
10 ) 《梦魇疯人院》--管理和惩罚是通用且唯一的手段
就剧情来看,这种反转模式早就被广大影迷所熟知并随时举一反三;就细节来看,杨·史云梅耶标志性的日常物品和嘴部特写均出镜率极低,而性狂想的表达更是用直观的锁链和刺耳的嚎叫代替了一贯的隐喻;就台词来看,略带说教式的连珠炮开始染上了喋喋不休的危机色彩。
《梦魇疯人院》的节奏非常拖沓,与其拿手短片的精湛丰富相比相当失手。
全片一直沉浸在对体制内外、意识形态、宗教神学、个人主义、怀疑主义所认知的危机中,以肉和部分器官代替了活物更是增加了这一压迫感。
海报上的酷刑一一实现,疯掉的是管理层还是平民百姓?
爱伦坡+萨德侯爵+杨·史云梅耶,又会是怎样一桌佳肴?
现代与古典的冲撞、车内的危险和窗外的危机,谁才是风景?
片中出现的重要实物有鸡、羽毛、肉、舌头、骨头、耶稣、食物、侯爵城堡、精神病院、房间,(值得庆幸的是成人用品在这里以隐藏的姿态被略过),如果通过这些不断重复出现的细节来解读这部影片也许更容易被理解、同时乐趣更多一些:肉:整部影片不断穿插着类似于短片的片段,用肉代替生物来展示他们的遭遇和未来。
鸟笼里跳跃的是一块块的肉;母鸡们吃掉一块块肉又下了一块块肉,这些被下的肉又回到搅拌机里搅碎供母鸡啄食等等。
悲观又愤怒的重复着自然界的铁规:即残忍的众生平等之感,包括那些崇高的和肮脏的。
鸡:白大褂在忙碌中穿梭于人群,洁白的羽毛漫天飞舞于视野之内,浪漫和祥和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姿态试图遮挡污秽,天使不存在,鸽子连想都不要想,这里只是一群忙着吃和被吃的母鸡在不知疲倦的咕咕叫着。
战争失败被异化的人用柏油沾满了鸡毛圈养在了地下室,人们每天所食的食物也尽是鸡肉。
母鸡不需要受精便可以产蛋,正好迎合了片中侯爵对圣母的鄙夷,处女生子。
母鸡吃肉下肉这一片段也符合了侯爵对大自然的谩骂:既是高尚的母亲也是妓女,来者不拒,博爱一切。
羽毛:人类既没有羽毛也没有厚长足以抵御寒冬的体毛,羽毛的出现有两个结果:挡住了男主角的视线,使他既看不到精神病院表象下的暗涛汹涌,也看不清地下室里被囚禁的人到底是医生还是精神病人。
羽毛在这里代表的是衣装:人们靠衣装判断环境优劣以及敌友是非。
舌头:舌头和肉的出场频率相似,这里所代表的便是言语自由和媒体传播自由。
每一根舌头就代表了一片灵魂、一种力量,它们可以作恶或行善,可以欺骗或劝解。
然而影片围绕在男主角身边所有的舌头都无法解答他的疑问,谁在说谎,真相何方?
每根舌头都有自己的帮派和首领,它们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不顾男主反对强行向他灌输自己的想法,男主角则像孩童一般听见什么信什么,最后噩梦成真被抓起来做了精神病院里的一份子。
这应属社会意识形态的力量,哪种力量更强大,便更能左右人民的方向。
骨头:本应是支撑起一个身体的根本,却因缺少肉和器官而失去了活力。
骨头像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本我状态,外界更多的经历会对它的本质造成改变。
耶稣:侯爵的一番无神论虽然有些偏激,但对上帝的认知尚可以接受。
宗教的作用应该只是为热衷于迷茫和软弱的人们提供一个开导的机会和哲学上的意见,更多的帮助人们相信爱并团结到一起,可惜它们最后总会形成一个坚持本教领导人的强大力量,被释放的医生说的好,“我们只用管理和惩罚”。
宗教和政治分不开,连他们的手段也是相似的,人民只能通过他们被允许看到的那部分来做出选择。
食物:侯爵在对付一颗豆子的行为充分体现了文明世界的虚伪,高贵即伪装。
当他们被涂满柏油沾上羽毛塞进地下室后,面对食物只有饥不择食的疯抢吞咽。
人只有在面对本能的时候才足够诚实,甚至是灵魂,也和食物一样,处于吞噬和被吞食的过程之中。
侯爵城堡、精神病院、房间:提供安全的同时也提供无偿的囚禁。
男主人公在自己房间里的梦魇终于成真,被硬闯进来的胖子抓进精神病院。
侯爵城堡和精神病院更是高度的相似,传播自己认为救世的思想并付诸于行动。
这些堡垒被史云梅耶用肉填满,随着心脏的跳动呼吸并颤抖,可以说是世界的运行规则或国家体制。
这种规则或体制在多数人或者说强大力量的引导下,如同怪物一般禁锢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想要逃脱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
我相信侯爵受的刑罚应该是脑叶白质切除术,最为严厉的一种。
本片展现的是一场严酷的斗争,包括个体与整体、自由与规则、神学与科学之间对抗的危机,与《魔诫坟场》有相似之处。
侯爵和医生都想占领精神病院并夺得男主角的所有权,这也应该与导演的国家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整部影片很可能就是男主角的一个梦,洒掉的杯座突然变干净等等不合理的细节也体现了这一点,但被叫醒也不是什么好事,你会被人大嘴巴子抽醒,然后继续可怕的噩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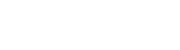






























片中对宗教的鞭笞是非常直接的,但是由萨德侯爵那样的人说出来,似乎也还是给了宗教一些面子。精神病院的势力转换,应该是有政治隐喻了,男主角就是典型地被各种政治力量利用的普通人,他的善良和同情心,在各种政治正确里都是不能容忍的,必须让他成为被管制的对象。那些肉本来就是死了的东西,还幻想着再次充满生命力,结果只能是死上加死,或者被做成肉馅,或者被密封在盒子里。它们本来就是统治者的赚钱工具,怎么能它们有生命、有自我意识。
还是看懂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世界是个疯人院,都是待宰割的肉
7/10,肉与欲与疯人院
Poe+Sade+Svankmajer
没看懂,加上史云梅耶开头的自述更迷惑了
8/10
#5800.杨大爷补番倒数第二部!这部格局和手笔都比之前的长片大很多!精华恐怕还真是杨大爷的导读,里面的肉动画真棒(原来89年的那个短片[Meat Love]是在为这部做研究啊哈哈哈)。剪进来的几个现代镜头,以及侯爵在黑弥撒时候那段反基督的演讲都很棒。与其说是在谈两种社会制度或者“第三条道路”,不如说是专注地解构法国大革命,以此来达到对后社会主义情境的反思。
2265
导演到底有多爱生肉!~~
性 时代感 中间穿插的那些定格动画效果很好 动画天才大师
感谢导演,转场画面的冲击让我成功改吃素。当身体和精神失去平衡,就离精神病院不远了,但是,当今时代,谁还没点儿精神病呢。
没意思
说实在除了感官上的刺激(不是色情哈),他要表达的意思还真没明白.
我曹,这片子神了
123分钟版本,开头有几分钟史云梅耶的导赏,说明主题是「现代文明对自由的压制与操控」。电影改编自两部的爱伦·坡的小说,男主角被送进疯人院的主线应该来自于《塔尔博士与费瑟教授的治疗方法》,这也对应被关押在地下室的员工身上被沾满了柏油(Tar,对应Dr.Tarr)和羽毛(Feather,对应Professor Fether)的遭遇,而暗示男主母亲在假死状态下被埋葬后又复活的情节应该来自于《过早的埋葬》,带着18世纪法国贵族装扮的侯爵原型应该是萨德伯爵。除此之外,电影来自原著小说的部分应该就不多了,而是辅之以史云梅耶式的粘土奇观(「生肉的跳跃与舞动」),行为艺术(往病人身上扔颜料进行「艺术创作」,以及联欢会上众人Cos《自由引导人民》)和对性行为的各类奇怪指涉(「整个故事是一场漫长的前戏」)。
暗黑政治小寓言 对宗教和自由的质疑 在新鲜隐喻上从来不让你失望
不疯魔不成活
冗长,定格成为装饰。观感近似平庸的东欧荒诞电影,史云梅耶无法驾驭长片也不需要长片。
隐喻讽刺都太直白明确了,但更大的问题是所谓“超现实”背后缺乏现实的根基,抛去标签式的“象征”之后空无一物,更像是一出政治小寓言。说白了史云梅耶还是在用他短片的创作思路拍长片,《贪吃树》这样格局偏小的还管用,但到这里就驾驭不住了,大段大段直给的台词简直就是走向了自己风格的反面,把人全删了只剩下肉,拍个《肉之恋2.0》都要更好。